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家里有不少搪瓷器皿,帶把帶蓋的杯、有蓋的缽、有蓋或無蓋的盆……它們都有些年頭了,但使用的頻率都不高,除了個別因磕碰掉了蠶豆大的搪瓷,其余都新得如剛出廠一般。
這些搪瓷容器只有一個是我自己買的,別的都來自親朋好友,每一個都有故事。
剛成家時,條件有限,做飯只能是用電飯鍋加煤炭爐,可煤炭爐經常熄火,老教師建議我們用電飯鍋下面條,吃時放點熬好的豬板油。
李老師老公在供銷社上班,熱情地告訴我們供銷社新進了一批搪瓷缽,蓋子可嵌入缽內,放豬油老鼠偷吃不著,數量有限,想買就給我預留著。我當即請他幫我帶買一只,想到好友一人在家,也是經常吃面條,就請陳師傅也給她買一只,我們兩家就有了兩只一模一樣的搪瓷缽。后來,我們的小孩也成了好朋友,我兒子在她家玩,看到那搪瓷缽,非說是我家的,讓我拿回家。好友騎車送我們娘倆回家時,還真的把盛著半缽豬油的搪瓷缽帶來了。我把自家的也拿出來放一起,我兒子扒拉來扒拉去,恍然大悟:“你們是好朋友,這兩只缽子也是好朋友。”他扒拉后,我們都分不出哪一只缽是自家的了。好友說不用分,等我把哪一只缽里的豬油吃完了,就把空缽給她,等過年殺豬時,再熬一缽油給我。后來,我們都不太愛吃豬油了,兩只缽子卻都留在了我家,都空著,上面印的牡丹花依然鮮艷漂亮。
家里最“古老”的是那個搪瓷杯子,上面沒有漂亮的裝飾,印著紅色的“為人民服務”幾個字。不清楚它為我們服務多少年了,只記得童年的我上學遇雨雪天時,中午不想回家吃飯,媽媽就讓姐姐用搪瓷缸裝上飯帶給我。姐姐回家一吃完飯,媽媽就趕緊把焐在鍋里的菜飯再熱一下盛進這缸里,蓋子蓋緊,用干毛巾裹好,再用媽媽的方頭巾包扎好。等姐姐拎到學校時,菜飯已經是溫吞熱了,但我吃得很香。吃干凈后把缸子往書包里一塞,放學時,書包里的缸蓋和缸子隨著我奔跑的腳步“乒里乓啷”響一路。
外公信佛,一輩子素食,外婆單獨做飯不方便,只好跟著吃素。媽媽有時燉好骨頭湯,讓我用搪瓷缸給外婆送些去。每次外婆都留我吃飯,總說:“我乖乖多吃點。”媽媽知道送去的骨頭湯多半都進了我的肚子,就又氣又恨地不允許我在外婆家吃飯,但外婆怎么會放我走?外婆去世后,這搪瓷缸一直也沒閑著。過年時盛熬好的豬油,豬油吃完不久,農忙時節到了,我們用它給地里干活的爸爸送飯。現在,這缸子在媽媽家、我和妹妹家端來端去,骨頭湯、魚湯、銀耳湯……哪家有了這些好吃好喝的,都用它裝上,一起分享。只是基本上我是坐享其成,因此,格外寶貝這已經被磕碰得掉了幾處搪瓷的缸子。
我結婚時,媽媽按習俗買了兩只印著紅“囍”字的搪瓷盆,可妹妹還是把廠里獎勵給她的兩只盆送給我,姑媽說盡管盆里都印著“囍”字,但兩只印花不一樣。妹妹把兩只盆分別放在媽媽買的盆下面,說:“這下看起來就一樣啦,四只盆是事事如意的意思,多好!”
我覺得四只盆太多了,可媽媽說過日子用得著的。用得著嗎?那時,我們已經喜歡用輕便的塑料盆了,那四只盆一直被我塞在口袋里,幾次搬家都小心翼翼地先把它們安置好。最近,心血來潮,把它們都拿出來派上了用場,看著紅紅的“囍”字,真是喜慶,彌漫著一種俗世的歡喜,家的溫馨倍增。
家里還正常“寄居”著一只大似洗臉盆的帶蓋搪瓷盆,是兒媳婦用來從娘家帶各種“媽媽牌”美食的,有一次居然裝了滿滿一盆的大骨頭湯。全家大快朵頤時,我都“諄諄告誡”孫子別忘了外公外婆的好,并佯裝:“這大搪瓷盆帶回去給外婆時,裝點啥才好呢?”孫子笑嘻嘻地說裝餅干,兒媳婦詫異:“要裝什么?回頭我還要用它從外婆家帶好吃的回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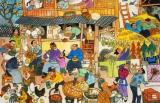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