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fā)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那些關于個人體驗、人生經歷的敘寫,呈現(xiàn)了她豐饒的內心世界,折射出不同時期法國社會乃至世界的風云變幻。弱水盡管有三千,我在這里只取一瓢飲。
諾獎授獎詞中說埃爾諾“勇敢而敏銳地揭露了個體記憶的起源、隔閡與集體壓抑”,這種“揭露”源于內心的不甘,是生命力的象征,賦予她反抗世俗、對抗現(xiàn)實的力量,構成她生存、生活的一種方式。
我們多少有些偶然來到這個不容我們選擇的世界,我們如何面對這一現(xiàn)實?安妮·埃爾諾及其父母選擇了抗爭。她的父母努力改變“骯臟、污穢、丑陋、惡心”的生存、生活環(huán)境,盡力為埃爾諾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以便讓她將來生活得比自己好;埃爾諾努力學習和工作;因“拯救什么東西的緊迫感”而從不同角度剖析、審視那些在性別、語言和階級等方面有著強烈差異的“細枝末節(jié)”,并予以個性化的呈現(xiàn);埃爾諾在采訪中宣稱自己是“黃馬甲事件”中的一員;還有,2020年在致總統(tǒng)馬克龍的公開信中她措辭嚴厲:“我們很多人想要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的食物、醫(yī)療、住房、教育、文化——能夠得到保障的世界……”林林總總,都是不屈的抗爭。
諾獎評會委主席安德斯·奧爾森認為,埃爾諾的寫作展現(xiàn)了一種“零度寫作”的傾向——不摻雜個人情感的客觀寫作狀態(tài),但同時又籠罩著一種“對她所脫離的社會階層的叛逆情緒”。這種叛逆就是一種抗爭。她的抗爭既有主動的一面,也有被動的一面。
她22歲時在日記中寫道:“我要為自己的出身雪恥!”表明那時她就產生了洗雪命運強加給她的恥辱社會身份的意念,雖然雪恥的方式方法和途徑不明確。后來,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繼承者》猶如“一道秘密指令”,引領她“沉入”深層記憶,“書寫在自己階級身份提升的過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恥,等等”。于是,寫作這種看似出世的逃避在埃爾諾那里轉化成一種積極的入世行為,一種能讓人看到社會不平等的政治行為,她肆意而不乏節(jié)制地揮舞起寫作這把“刀”,殘酷撕開血淋淋的面紗,從縱深維度直面廣闊的社會現(xiàn)實。
在她生命的某一時刻,一直“認為是恥辱所以深藏起來”的一切突然之間被重新賦予了難以釋懷的苦澀、感傷與憂憤等意義,“值得被重新回憶”,于是,她驅動文字,包括大量冷靜的幾同冒犯的敘事,描述、展現(xiàn)個人記憶與人們集體經歷之間的微妙互動,讓人們從“簡單的激情”中見到自己,重返日漸逝去的社會和時代,以召喚內心深處的渴念,展開與時代的對話,探討時代難題如女性不平等。在這里,激情不只是寫作的起點,還是寫作、呈現(xiàn)本身。
她坦言:“我寫《正發(fā)生》是為了保存對數(shù)百萬女孩和婦女遭受的暴行的記憶。”這種以描述、呈現(xiàn)包含屈辱在內的經歷為方式的抗爭對埃爾諾本人來說,首先是一種自我救贖,是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之后一種精神重建和回歸。如果不把那些經歷寫出來,她就難以安寧。而在《那些年》中,她認為正是那些“洗去恥辱印記的記憶”,為她勾勒了一個文學、知識以及政治的前途,讓她能夠重新解讀、闡釋自己不同階段人生軌跡以及她個性的不同構成維度,也不斷治愈她內心的傷痛。
埃爾諾一直在抗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階層叛逃者”(transfugedeclasse)。這一名詞來自于哲學家尚塔爾·雅奎特,指從一個階層階級向上流動至另一個階層階級的個體。transfuge”在法語中有“逃兵”義,而逃兵,既為己方所不齒,也未必會被對方接納,因此,“階層叛逃”不只是指身份改變之過程和結果,還含有個體“卡在兩個世界之中”的尷尬心理和精神狀態(tài),譬如她曾背負父親的不理解,長期在“努力離開母親”和“深愛母親”的矛盾中掙扎。她通過不斷的寫作,以實現(xiàn)她精神上的“叛逃”和心靈的皈依。
當然,這種階層叛逃不只是她,還包括她的父母以及不同階層等,在為她贏得1984年勒諾多獎的《一個男人的位置》里,她說:“最讓父親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奮斗目標,那就是讓我進入一個曾經對他不屑一顧的社會階層。”描述底層民眾改變命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
她擅長在日常記憶的敘事中融合多種情緒,既拓展了內容,又使作品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評委會相關負責人認為埃爾諾在文學上的共性適合每位讀者,她一系列叛逃行為和作品所蘊含的抗爭精神應該從屬于這里的“共性”。當然,她作品中能夠讓受眾引起共鳴的“共性”遠不止這些,譬如下面這段平實樸素的敘事就讓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那里的人們,總是在親朋的婚禮或是領圣餐前的幾個月前就開始計劃起來,他們提前三天就留出自己的肚皮以便讓自己能夠在婚宴上或領圣餐儀式上吃更多的食品。”個體日常生活中的體驗、經驗與人類的體驗、經驗相連相通,許多類似的敘事描述猶如被鏡頭捕捉到的日常畫面,能喚醒那些有過類似童年經歷的人的記憶。
她敘事直白,直白得近乎殘酷,但又給人靈魂以震撼。在《一個男人的位置》里,她只是把父親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他的愛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經歷過的事用“給父母寫信報平安時用過的筆調來描寫”。這種避開先前“主觀視角”的抒情書寫,而代之以平實敘事,能夠“將敘述的中心簡化為一種20世紀晚期靈魂的肖像”,是為突破“社會階層之間的隔膜”而作的努力,本質上仍然是抗爭。
獲獎后,埃爾諾表示:“這次的諾貝爾獎是一種責任,我要繼續(xù)與不公正作斗爭。”而且表示,她會初心不改,會抗衡到最后一口氣。生命的抗爭與文化的抗爭相互激發(fā),使得個體的經歷融入法國社會發(fā)展過程之中,獲得強大的精神依托。
她的抗爭,她的人生體驗、生命記憶遠不止承載個人豐贍的情感、困惑、感悟、情境乃至幻想。埃爾諾卓有成效的抗爭,不只是因為她出眾的才華,更源于她的深情,對父母對人生對女性對世界的深厚感情。
埃爾諾基于自己的情感、立場、趣味與理論預設,對個人記憶和社會現(xiàn)實進行富有個性化的選擇與建構,以廣闊的視野和跨文體的形式,把廣闊而豐富的社會歷史和有聲有色的立體法國鑲嵌在個人化的體驗和記憶之中,使之在美學方面得以縱深拓展,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審美內涵。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她寫道:“……父親總是從掛在廚房里的地圖上時刻注意著部隊進攻的情況,注意著戰(zhàn)局的變化。”還認為:“戰(zhàn)爭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譬如人們在咖啡廳不再喝蘋果酒而改喝葡萄酒,女孩子也不再喜歡在農場干活的小伙子。
正是因為她那些富有個性特色的生命體驗、個人記憶、人生經歷融入階級與國族敘事而承載許多人的記憶,所以不止一代人能從她的敘事、呈現(xiàn)中身臨其境。也正因為她不斷建構起讓讀者置身其中、重構自我的世界,所以,埃爾諾的作品不只是文學之作,也是歷史之作、現(xiàn)實之作、思想之作,而且還是生命之作。
今年諾獎以“暴露”的名義肯定埃爾諾頑強不屈的執(zhí)著抗爭,彰顯的是無比尊貴的生命價值。內容的抗爭性和敘事的高超技巧猶如車之兩輪,相依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了她作品的經典化。
每一位讀者都是帶著自身的人生閱歷和特有生命體驗等走進具體文本的。閱讀優(yōu)秀文本的過程,是讀者與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不斷展開對話的過程,是一個真切的生命去感受另一個鮮活生命的過程,一個靈魂呼喚另一個靈魂的過程,因而是使文本復活的過程。埃爾諾之所以享有盛譽,一個重要原因是滲透在字里行間的抗爭精神能夠豐富讀者的生命內涵,激活讀者的生命活力,讓他們從那些日漸淡忘的記憶中召回失散的靈魂,能夠“提高人的歷史文化意識,點醒人的真實生命,開啟人的真實理想”。
對一個以創(chuàng)作為職業(yè)的作家來說,能夠用諾貝爾文學獎來肯定自己的創(chuàng)作,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但我相信,對安妮·埃爾諾這樣級別的作家,讀者的閱讀、讀者在不斷延伸的時空維度中的接力閱讀是更讓她快意的事。既然閱讀是向這位老人致敬的方式,那就去讀她那些可能讓自己驚艷的作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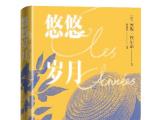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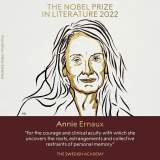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