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這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冬至夜懷湘靈》。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有注:湘靈,居易早年之戀人。
年少之時,白居易曾住在汴水邊的東林草堂,湘靈是其鄰家女子。《宿縣文化志》有記:白居易故居,在宿縣(今宿州)北二十里古符離東菜園,名曰東林草堂,遺址猶存。此地曾建有白公祠。
白居易父親白季庚,官拜徐州別駕,職充徐泗觀察判官。有學者考證認為,當時屬于徐州轄區的埇橋可能即為其任所。據《大清一統志》,埇橋又名符離橋,亦名永濟橋,跨汴水。為躲避藩鎮割據之亂,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歲的白居易跟隨母親一路顛簸,從鄭州的新鄭縣(今河南新鄭)遷到埇橋(今屬安徽宿州)安家。在符離,情竇初開的白居易遇到了初戀情人——小他四歲的鄰家女子湘靈:“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蓮。何處閑教鸚鵡語,碧紗窗下繡床前。”(《鄰女》)這段戀情讓他畢生難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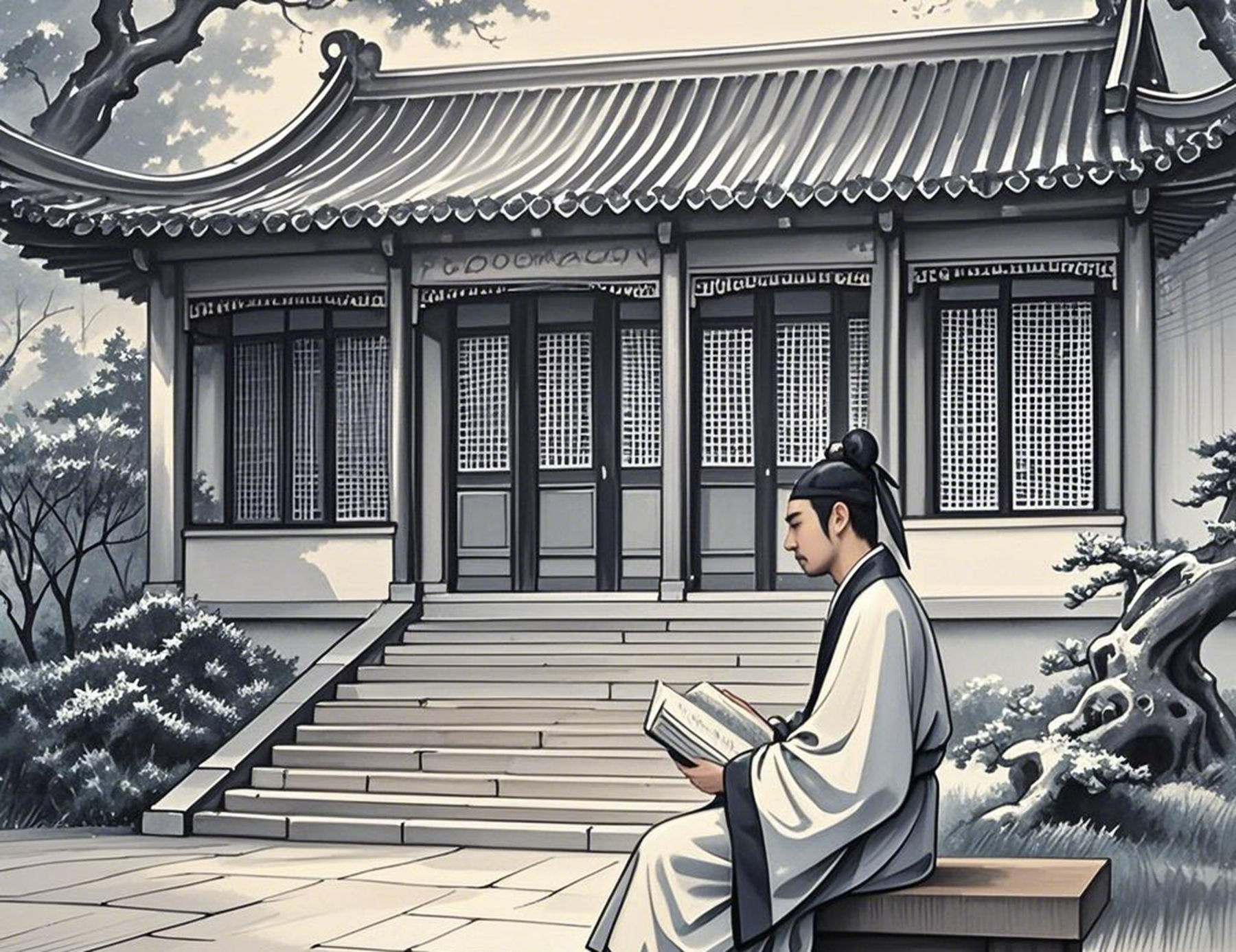 東林草堂讀書圖(AI生成)
東林草堂讀書圖(AI生成)
熱戀:“兩心之外無人知”
“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惟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后期。”(《潛別離》)
這首詩是白居易為告別湘靈而作。因時局動蕩,白居易被家人安排到南方遠游投親。擔憂此去難歸,詩人萬般無奈。
顯然,這是一場凄美的戀情。兩情相悅,意深情癡。只是,一個出身于官宦之家,一個則是平民之后,礙于門第觀念和禮教習俗,他們偷偷見面,暗自相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回”“愿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長相思》)在《寄湘靈》中,白居易寫道:“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回頭。遙知別后西樓上,應憑欄干獨自愁。”
貞元二十年(804),已在長安作了校書郎的白居易,到符離搬家,遷至長安。此時,白居易已經三十出頭,尚未成家;湘靈二十七歲,還未出嫁。這在當時,都已屬于超級“大齡青年”。兩個有情之人,為何不能終成眷屬呢?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白居易的母親強烈反對這門親事;也有人推斷,可能是白居易的父親或家族不認可這門親事;還有人認為,是女方家長擔憂女兒受到委屈而不允。總之,無奈之下,兩人最終沒能走到一起。
“生離別,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發。”(《生別離》)
無論是“潛別離”,還是“生離別”,這一轉身,就是勞燕分飛,各奔東西。留下的唯有離愁別恨,只有不絕如縷的相思之情。
難舍:“唯不忘相思”
或許,初戀的熾熱,烙下了太多太深的印痕;或許,內心的渴求,催生出太長久的懷念。于是,那份刻骨銘心的純真情愛,那種難以化解的纏綿相思,自然而然地滲透在那些傳世的白居易詩句中。
白居易深深牽掛著湘靈,除了《冬至夜懷湘靈》,其《夜雨》寫道:“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
封建時代,婚姻大事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功名不能放棄,親人不敢得罪,對湘靈又不忍放手,處于矛盾的焦點,白居易無法逃避,找不到出路。愁腸百結,無比苦悶。其實,在當時的環境里,受到傷害最多最深的還是湘靈姑娘。逝水流年,韶華不再,棒打鴛鴦,佳期無覓。
因為苦戀湘靈,白居易一直不娶。在親友的勸說和撮合下,直到三十七歲才和名門閨秀楊氏小姐結為夫婦。盡管夫人端莊、賢淑,但是白居易對湘靈的思念依然不減。
與“生死兩茫茫”的絕然無望不同,那種身不由己、難舍難分的訣別,讓人痛不欲生,無處安放。
白居易的深切相思之情,多少還有一些對于湘靈的愧疚吧。這種無法消弭、難以釋懷的苦悶和牽掛始終伴隨著白居易,一直到老,真可謂“身與心俱病,容將力共衰。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偶作寄朗之》)
有學者稱:《白氏長慶集》存有白居易與鄰家女湘靈戀愛的詩14首(黃世中《中國古典詩詞:考證與解讀》),胡秋源《詩話埇橋》則列出15首。
 張紅心/攝
張紅心/攝
絕唱:“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一生留下近三千首詩作,在我國詩歌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生活在符離的那些日子,對白居易的創作和人生產生了很大影響。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因為接近下層民眾、體察民間疾苦,白居易憫恤民生,痛砭時弊。從“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賣炭翁》)、“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觀刈麥》)“回看歸路傍,禾黍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月夜登閣避暑》)、“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等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之二)的剛腸直氣。
在白居易的筆下,還表現出對婦女命運的關注和同情。在《上陽白發人》中,詩人道出了一個白頭宮女的悲慘遭遇和怨曠之苦:“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婦人苦》一詩則委婉地揭露了男女之間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最后發出感嘆:“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在《井底引銀瓶》中,詩人用凝練的語句描述了一個私奔女子的不幸遭遇,最后勸誡道:“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長篇敘事詩《琵琶行》是一首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詩人聽了琵琶女高超的彈奏,并得知琵琶女的飄零身世,聯想到自己“忠而被謗”、蒙冤被貶的遭遇,嘆息不已,淚濕青衫,在情感上產生了強烈共鳴:“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白居易能夠描繪出琵琶女的感人形象,關鍵在于他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傾注了深切的同情。難能可貴的是,雖然“身為本郡上佐”,可是白居易不拘于封建禮法,對平民百姓平等相待,甚至對“似訴平生不得意”的琵琶女產生了同病相憐之感,體現出真摯的人性關愛。
因為“深于詩,多于情”(陳鴻《長恨歌傳》),以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愛情故事作為創作題材,白居易的內心情感得到了一次絕好的宣泄機會,就此成就了一首蘊涵深永、雅俗共賞的千古絕唱:“……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長恨歌》)
這首詩作之所以凄婉動人,傳唱不衰,除了獨特的主題,一以貫之的平易淺近詩風,更是因為詩人在字里行間傾注了他和湘靈之間的真摯情感。看似敘事詠史,實為感傷抒情:那種難舍難分的愛戀、那種纏綿悱惻的相思、那種生離死別的悲痛、那種無法排遣的永久遺恨,分明是詩人在感嘆自己啊!
如今,東林草堂成為宿州新汴河景區一處打卡點。獨自漫步水邊,輕輕吟誦那些世代相傳的經典詩句,沉湎其間,仿佛時光倒流…… (李學軍)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