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我與潛山籍作家徐迅相識相交已經30多年了。他個子高挑,身板單薄而挺拔,頭發烏黑微卷,偶爾有一兩綹不安分的卷發垂在白凈的額頭上,他總習慣用食指把它鉤到原位,然后又用中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鏡,鏡片后是一雙睿智的眼睛,顯得干練。讀了他的早期散文,覺得是靈氣加才氣,更覺得他的散文創作富有創新性,他突破了山水田園散文的寫實性,往往由一個或幾個意象生發出來洇染開來,插上聯想和想象的翅膀,在“虛”處潑墨,虛實相生,因而他的散文顯得空靈而有新意。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迅只身到北京工作,后來擔任《陽光》雜志主編。2001年冬天,我在北師大參加教育部“跨世紀園丁工程人才”的培訓,這是我同他在北京的第二次晤面。記得那天見面,他送了我們他的散文新著《大地芬芳》和幾期《陽光》雜志,之前有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想象一株梅》。席間,他談到自己的創作和與高校學生分享他的創作體會等情況,感覺他的創作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后來,我斷斷續續地在《人民文學》《新華文摘》《散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大報大刊上看到他的新作,在《語文學習》上看到他的作品被推薦為中學語文教材。盡管這樣,但當有一天比較全面獲悉他的創作成就時,還是突然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他著有散文集《皖河皖河》《徐迅散文集——響水在溪》《徐迅散文年編》(四本)《半堵墻》《春天乘著馬車來了》《染綠的聲音》,詩集《失眠者》、小說集《某月某日尋訪不遇》《夢里的事哪會都真實》、長篇傳記《張恨水家事》等,被各大出版社收入文集的達260余種。《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報刊對他散文、詩歌、小說、人物傳記評論的文字達90余篇,其中對他散文集和單篇散文評論的文字達86種之多,評論的專家、學者、作家達70多位!諸多評論中,孫仁歌發表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1期題為《“宅”在皖鄉皖河樂水意象深處的裸魂——“徐迅散文年編”釋讀》寫得厚重而有分量。該文以文藝理論家的視野,文學批評家的視覺,學問家的嚴謹規范,對徐迅鄉土散文“樂水”的主體意象,“記述的”“藝術的”“中國式的”的品性,“人性化”的意味和一顆真誠的“裸魂”的創作成因進行了精細精美的釋讀,讓“徐迅迷”們醍醐灌頂。不過該文結尾處從散文的“密度”“彈性”“質料”對徐迅散文也提出了批評意見,但我不敢茍同。我認為,密度與彈性成反比,密度越大,彈性就越小,這就是實與虛的關系,太實了,就少了空靈,就擠占了讀者想象空間。質料與彈性成正比,語言的質感越新奇,給讀者的想象空間就越大,彈性就越大。工筆式的《瓦爾登湖》(梭羅)固然美,寫意式的中國散文同樣美,我倒喜歡讀寫意式的中國散文,這種空靈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任由馳騁。
徐迅的散文顯然屬于后者。
徐迅之所以能奔向散文創作之巔,其原因有三點:一是他守得住寂寞,在散文沃土上精耕細作。誠如《裸魂》所言,徐迅也算是耐得住寂寞了,這些年來,很多小說家紛紛“觸電”,很多散文家、詩人紛紛改弦易轍寫小說,但徐迅一直堅守著散文這塊麥田地,人在京城心在皖,一直默默地把心“宅”在皖鄉皖河過散文的日子;二是他對散文創作的執著。散文是他的真愛,對她的愛是專一的,與散文進行對話已經是一種常態,不可或缺。正如他自己所說:“散文是心靈缺憾者的藝術,生活在現代文明里留戀鄉土,懷念鄉村——只要不虛偽和濫情,卻是人們心靈缺憾時的一種精神的企冀,是藝術對心靈的一種補充。”三是他的真誠與才氣。真誠是他散文的魂,才氣是他散文的雙翅,他那獨特的感悟、豐富的聯想、奇特的想象、超常的語詞搭配以及那化平實為新奇的“喻體”給讀者以清新之美、靈動之美、飄逸之美、哲思之美,總讓讀者暗暗叫絕。
在今天看來,徐迅的散文創作對引領當代散文創作是有積極意義的,為此,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批評家發掘其散文價值就顯得必要而迫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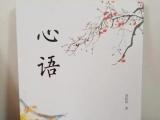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