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作家凌澤泉有兩副筆墨,一副寫小說,一副寫散文,散文是他的主業,小說是他的副業。他在散文方面的創作成績斐然,已然出版了散文集《立體的鄉愁》《種植鳥鳴》,還有這本新竣的《抒情的鄉村》。由此不難看出,身居都市的作家,他的精神故園在鄉村,他的情感寄寓在鄉村的草木氣息,他濃郁的鄉愁在故土的風物和人事。
《抒情的鄉村》多以回憶性的筆觸深情重溫昔日的這塊心靈沃土,融歲月的情愫、感觸、痕跡入鄉村的萬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鄉村“風物志”,也是作家主體情感真誠流露的“心靈史”。具體而言,這部散文集以下幾個方面令人稱道,頗具特色和個性風采。
其一,抒情主體情感的真摯、細膩、溫婉。“修辭立起誠”,散文作為最重要的文類之一,因為其素材的真實性,因而對創作主體情感態度的真誠性要求是更高的。凌澤泉的這部散文集可以說很好地踐行了散文寫作這一文體成規。我和凌澤泉同為合肥市作協主席團成員,開會的時候經常交流對生活、對文學的看法,他是一個真性情的人,臧否現實、文學,發表對當下的看法,頗為真誠,不似我這般學院派的“理性”。他的真誠來源于他自己內心堅守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傾向,這其中,就有他對當下物化現實的拒絕,對欲望化世俗化功利化社會現象的反感,而他賴以抗衡世俗現代性的感性力量和心靈資源來源于他從故鄉的風物及其人情、倫理、鄉俗、生活方式所習得的思想志趣和審美精神。作家來自鄉村,熟悉故土的一草一木、山川河流、風土人情、倫理禮俗,在這樣的鄉村語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心靈無不烙刻著鄉村的經驗和情感以及由此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當作家在現實中感到困惑、疲憊的時候,他深情回眸昔日的鄉村,不僅僅是安頓自身躁動的靈魂,也寄寓著內心對鄉村、對故土的虔誠,對往昔生活及其觀念的深情固守,正如作家在自序中所說:“我試圖讓自己的文字能夠氤氳些草木的氣息,即便是對鄉村的一次次張望,也心懷虔誠。”
《抒情的鄉村》共分五輯:《槐花細細開》《蛙聲筑樓》《秋色斑斕》《冬陽和暖》《時間有痕》,在時序的遞嬗、季節的轉換中抒發了歲月流逝的印痕,尤其是凸顯了創作主體對鄉村情感真誠、細膩和溫婉的抒發。春天的布谷啼播、槐花細開、桃花灼灼、山菇撐傘、春山鳥語,無不顯示出鄉村萬物蘇醒的精氣神;蟬鳴蛙聲、梔子芬芳、夏荷浮翠,無不映射出夏日鄉村的勃勃生機;秋色更是斑斕,扁豆花開、棉花云白、金桂彌芳、蘆花似雪,還有很多詩意的農事,喚起多少潮濕而溫潤的鄉村記憶;冬天檐下臘味、劈柴的人生、年飯里的親情、裊裊的炊煙,勾勒出充滿人倫色彩溫情而和諧的鄉村生活圖景。這些生命感受在城市生活中是遲鈍的、麻木的,城市因遠離故土和自然,也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生命的原初體驗和詩意的審美情懷。賈平凹有一句話:“你怎樣對待自己,就怎樣寫散文。”說的是寫散文要真誠,不能弄虛作假,也不能得過且過。在我看來,凌澤泉深諳真誠是散文的生命,他的散文就是寫他自身真切的生命體驗,真誠而又自然。
其二,“萬物有靈”的情感化敘述與訴說。通讀散文集,除了上面論及的抒情主體的真誠以外,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抒情的鄉村》賦予了審美對象“萬物有靈”的人格化、情感化的主體性品格。鄉村的草木、風物、歷史不是被動的審美客體,而是充滿了如人一般的靈性、情感和欲望。恰如扉頁上所言,“每一座山峰,都在訴說著纏綿悱惻的故事;每一條田埂,都在講述著美麗浪漫的傳奇;每一條河流,都充滿了蔥翠欲滴的詩意;每一處村莊,都承載著輝煌而又沉甸甸的歷史。”文集中的多篇散文對鄉村物象、事象的描摹充滿了大量人格化修辭,這里不妨援引一段原文:“飛舞是鐮刀的夢想,春風輕撫窗欞的那一刻,鐮刀最先窺到;燕子回到房梁之上,鐮刀第一個發覺。那月牙狀的鋸齒里,去歲的草香開始復蘇,舊歲的麥香與稻香也被喚醒。鐮刀走下墻壁的步伐里,有著抑制不住的激動。”不僅僅是人格化情感化地呈現對象的主體性,散文中還藉由風雨、青瓦、桃花、布谷、麻雀、斧頭、炊煙等的視角打量鄉村的日常。這些視角的開拓,不僅讓鄉村世界洋溢著盎然的詩意,同時也讓尋常鄉村“存在者”的“存在”具有了別樣的內涵。這種情感化人格化的書寫,不單單是敞亮了審美對象的主體性,也是散文家本人生命意識和生命觀的一種展現。在作家眼里,鄉村的萬物都是有生命的,每一個鄉村“存在者”都飽含著豐富的情感,見證著鄉土歷史的演繹和時空的滄桑,見證著鄉土社會倫理、文化、風俗的時代變遷。鄉土萬物“追求”的是個體無拘無束的自由生命,是大自然的順化和樂天知命的達觀,而這一切似乎在世俗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中離我們原來越遠了。所以,鄉村的生活經歷和體驗,引發了作家無限的“鄉愁”。作家的另一本散文集就是《立體的鄉愁》,而這本《抒情的鄉村》更是把“鄉愁”引向綿邈和深邃,也是作家在藝術中構建自我的精神家園,只有在故土的山水逍遙和風物流連中才能暫時忘卻塵世的禁錮、煩憂,只有在心靈世界里有一方“精神飛地”,才能構筑內心的堤壩,抗衡物化世界對人性的壓抑和侵襲。
其三,長短相宜的篇幅,素樸且詩意飛揚的文字。散文集多是篇幅不長的抒情短章,只有寫鄉村的文化、掌故、歷史的那幾篇稍長一些。篇幅短小,但并不意味著內涵的浮淺,“尺幅千里,必當言微意深”。中國古典散文也頗多抒情短制,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張岱的小品文《西湖七月半》等,現當代文學中的魯迅、朱自清、周作人、楊朔也有許多膾炙人口的短篇抒情散文經典。當然,《抒情的鄉村》并不追求多么深邃的思想主旨,而是更多地抒發對故鄉的深情,鄉村的每一個風物、每一個細節、每一處農事都能觸動作家敏感的內心,引發他對故土的相思與緬想。抒情短章多是隨性而發,依著自己真實的內心,滿蘊著濃郁的鄉愁,充溢著對鄉土真摯的感情,捎帶著作家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回憶性闡釋,同時也深切體現了抒情主體個性化的生命意識與審美觀。
第五輯“時間有痕”里面的篇幅稍長,尤其是對故土歷史的人文考察,不是簡單的歷史系譜學追尋,而是交織著鄉村的回憶性想象和鄉情民俗的熏染。《深情燒脈崗》《豪邁的山水情懷》《風過安溪村》等篇幅將“時間”的痕跡深情地融入散文的字里行間,讓讀者在領略自然山水、田園的基礎上,感受鄉村的人文底蘊、歷史掌故、文化遺存甚或美麗的傳說。《抒情的鄉村》里的文字也是滿貯詩意,比如:“露水瀼瀼的秋夜,月光靜悄悄地漫下來,伏在枝柯間,一朵朵閑云也飄然而下,柔柔地鋪開潔亮的被褥。想來,這枕月衾云的枝柯,竟也有著如此的浪漫。”不難看出,文集中的文字既典雅不失風致,富有詩意,深受古典文學的影響,又面對當下活色生香的現實,具有素樸靈動的質地。
有人感嘆,中國當代文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城里人下鄉”和“鄉下人進城”。城里人下鄉指的是知青文學,而鄉下人進城則是伴隨著中國現代性的歷史進程,鄉村青年進城的生存史與心靈史的文學書寫。凌澤泉當然屬于后者,他雖肉身進了省城合肥,但他的精神仍然屬于鄉村。他對鄉村的回望與深情,不是知青作家“外來者”的眼光看待鄉村,而是有著非常真切的鄉村生活經驗與昔日鄉村生活的價值認同與審美感知。由此,他對鄉村的抒情,是“貼地”的飛行,是及物的抒情,是將主體深摯的情感、歲月的情愫融入到鄉村萬物的抒懷。這種情感打通了過去與當下的壁壘,由現實出發而回溯往昔,或由回憶再回到當下,其自由的、審美的靈魂穿梭于它們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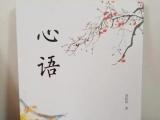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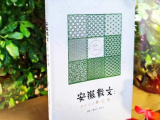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