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牽動億萬人心的高考又要到了。說到高考,生于1960年代的我,個中滋味至今難以忘懷。
我小學和初中一直在家鄉學校就讀,當年中考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績被海陽中學錄取,我和家人都為此感到高興,畢竟汗水沒有白流,雖然與中專和休寧中學有20多分的差距,但能進入海中也是鄉下學子夢寐以求的。
當時因學校建新教學樓,我們高一開學推遲了一個多星期,開學前幾天,家里特意找師傅打了口木箱,我早早備好衣被、日用品,聽說高一就要分文理科,且自己文科好些,便把初中歷史地理教科書全帶上,一時將木箱裝得滿滿當當,入校的心情有點迫切。
進入偌大的海中校園,對我這個15歲鄉下少年來說,猶如入了大觀園,什么都稀奇。報到時,我被分入理科(2)班,內心有點失望,送我到校的哥哥說,你中考數理化還可以,再說理科高校多且錄取率高些,讀理科蠻好,別多想了。我沉默不語,只得聽從命運的安排。還好,后來知道我所在的理科(2)班是重點班,年富力強的化學老師趙澤奇兼班主任,口碑好且水平高,其他科目老師都是“高配”,應該是對這個班寄予厚望吧。
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學生人數多,錄取率低,考取本科的寥寥無幾,專科也沒幾個,中專都不多,一旦考取畢業后就包分配工作,端上“鐵飯碗”,很誘人。我們班同學大多數來自農村,雖說尖子生入了休中,但能進入重點班也是各學校比較好的苗子,競爭壓力可想而知。我也一樣沒退路,在我初中還沒畢業時,二哥就頂班招了工,而我一旦考不上就只能回家務農了。
所以,從入校那天起,我每天天沒亮就起床,出操、早讀、上課、自學,晚上弄到11點多才休息,日復一日,簡單枯燥,硬著頭皮也要往前闖;教室、食堂、宿舍三點一線,寒來暑往,一年到頭除寒暑假回家外,周日都不休息,一心撲在學習上,不可謂不努力。可能是天賦不夠,我學習成績徘徊在中游水平,尤其是對數學物理這兩門課不感冒,雖多次請教老師或同學,反復鉆研做題,但毫無長進,每次考試都不及格,這個硬傷到高考前都沒法解決,由此留下后患。
一晃兩年高中生涯就結束了,那時實行高考預考制,預考達線才能參加高考,因我成績尚可,這一關算順利通過。7月7日,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入堪稱人生重要關口的考場,三天緊張的考試,雖盡了最大努力,但第一次高考,便名落孫山,距中專線差不少分,尤其是數理化分數低,也是預料之中,況且班上那年也沒有幾個入圍,因此心理上還過得去。
回家后,戴著近視眼鏡的我就只能干農活了,時值盛夏,挖地、割稻、做家務活,樣樣都得干,有時還要起早貪黑,原本黝黑的皮膚曬得更黑了,這個暑假第一次體驗到做農事的艱辛。自小就一直輔導我學習的哥哥問我,你眼鏡近視,當兵不夠格,干農活干不出頭,以后該怎么辦?我說,復讀一年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人生能有幾回搏”,1983年10月,我又踏入海中補習班行列,學校不安排住宿,好在碰到好心的初中部徐季婉老師,她老母親家里有空房,無償給我們住宿,解了我和同鄉同學的燃眉之急。那時的補習班匯聚了休中和本校的落榜生,競爭更加激烈,學習氛圍更加濃厚,壓力也與日俱增。
又是一年寒窗苦,我滿懷信心參加第二次高考,得了403分,與中專分數線差1分,仿若晴天霹靂,這打擊無疑太大了,欲哭無淚。哥哥說,后期有可能降分補招,到時看運氣吧。還真如哥所料,有補招名額,我想差一分應該有希望,哪成想,左等右等沒消息,便趕到招生辦查詢,招生辦的人說,你志愿沒填好,第一志愿填了蕪湖農校的同學402分就錄取了,原來我第一志愿是省輕工學校。到手的工作沒了,這個消息再次打蒙了我,那天如何回到家我都不知道,為此還偷偷大哭一場,那種悲傷的心情可想而知。
這次高考,補習班的同學考得不錯,考上本科的有好幾個,4個要好的同學中查旭、吳新和如愿考取心儀的大學,沈文生也考取了中專,就我再次落榜,心有不甘。
經歷了這個打擊,我精神萎靡不振,很長時間才緩過神來,后來,哥哥原本要我在當地小學當代課老師,我還是想去復讀再搏一把,就在準備去時,恰逢全縣招收鄉鎮干部,還是全部轉編的,我立刻報名,一考就中。1996年,我通過參加函授學習取得了大專文憑,但成色差點。
光陰似箭,離開學校40年了,雖然沒能如愿上大學,但拼搏過、努力過,值得。如今我快到退休年齡,雖算不上事業有成,但工作穩定,家庭和睦,女兒考取了理想的大學找到滿意的工作,也成家生女。每每跟女兒聊起高考我總說,你們是趕上了好時代,當年要是有現在的錄取率,我可是二三本的大學生了,這沒上大學的事成了我唯一的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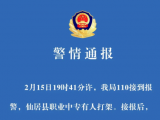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