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小區有好幾種野菜是可吃的,薺菜、野蒜、馬蘭頭、小鵝腸。薺菜最多,從開春一直到春深,一茬又一茬,似乎是天天可挑的。春風催著薺菜長,挑完了又潑潑地長。薺菜包餃子吃,吃不厭;野蒜也多,混在草窠里,綠綠的,顯眼。野蒜要向深里挖,野蒜頭嫩且香。野蒜用老抽泡了,當調味品,也可當小菜吃,挺香的;馬蘭頭挑的人不多,綠中泛紅,好看;至于小鵝腸,知其能吃的不多,可確實好吃得很,清炒、涼拌都不錯。
若在小區散步行走,略有閑心,總有野生的草或菜和你打招呼。小區的野生植物多,幾十上百種肯定是有的,除了剛說的幾種好吃的野菜外,婆婆納、律草、牛筋草、益母草、車前子、奶腥草……我能叫上名字的就有一堆。
這些野草(菜)是土著,比住進小區的人都要早,查查資料可知,腳下的小區是建在一個丘陵地塊上的,地塊多元,有河流、有塘口、有農田,野草(菜)亦多元。多元的野草隨泥土而存,斬草除根的事做不了,它們就活了下來,和小區一道,和小區的紅男綠女、老老少少一道。
城市擴張太快,野草的領地一再被侵犯,它們得學會生存,生存到城里去。
小區無疑是個百草園,留心或不留心大可給人以驚喜。一天,我在眾多的野草中發現了灰灰草,這叫藜的家伙,葉子灰綠,在綠色的簇擁下羞答答的。灰灰菜也可吃,嫩葉炒或“渣”都爽口,有趣的是,灰灰草的葉面用手摸上去,好像有層細塵,好玩得很。灰灰菜能長得高大,稈老了可作手杖,謂之藜杖。有詩句說:“古木陰中系短蓬,杖藜扶我過橋東。”灰灰菜是古老的植物,在地球上也不知生存了多少年,可植物又有多少不是古老的呢?

我的孫子上上喜歡植物,我常帶他在小區里識草,自然也挑薺菜、挖野蒜之類的。我和上上說灰灰菜事,說藜在《詩經》里的表現: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萊就是藜,藜嫩葉可食,藜就是灰灰菜。上上聽不懂,倒是說:我們不傷害灰灰菜,長個藜杖,送給太太。上上很是天真,我心中暗生歡喜。
又一天,我在一空地上發現了一蓬走藤的植物,葉若山芋,藤卻是青翠的,我叫不上名字,但我敢肯定,不是我們這當地土生土長的植物。我多方打聽,知道了它的名字,折耳草,又叫魚腥草。摘一片葉子聞聞,果然是一股子魚腥味。
據我所知,折耳草云南、貴州人愛這一口,涼拌、清炒都吃得“烈”。再后來,我發現有一女子采摘折耳,一打聽,女子是貴州人,折耳草是她專從貴州捎來的,折耳草竟不擇地,在小區有了一塊領地。折耳泛著“好聞”的魚腥味,“好聞”是貴州女子說的,這一定是她的故鄉味之一。
小區的人來源廣,五遠八遠地來入住,語言南腔北調,連植物也多樣了起來,有趣,也符合規律。植物不行走,人可捎上,比如來自貴州的折耳草。
我一直在記憶里摳著小區里野草的名字,對它們的模樣我是熟悉的,它們都曾在我故鄉的田埂、野地上生活過。我開動腦筋,還是叫上了一些名字:泥胡菜、蛇莓、油荊芥、大薊、小薊、蒲公英、馬鞭草、田蔙花、馬齒莧、癩猴菜……每叫上一個名字,親切感就在我的心中升起,讓我的心軟軟的、濕濕的。
事實上,小區的野草我能叫上名字的也僅十之一二,大多數是識其面不知其名,這也不能責怪我的記憶力。在農村生活的那么些年里,野草太多,我識不全,包括我的父輩們也不是能叫上全部名字的。能叫上名字的要么是人畜可食用,或者有藥效,或者就是有毒的。識得有毒的野草很重要,盡管饑不擇食,送命的還是不能向嘴里塞的。
在小區行走,紫花地丁開得真好,紫色的花朵,翠綠的葉子,一小片一小片地呈現,引得蜂子們忙個不迭,盡管有春梅在它們的頭上罩著紅、沐著香,它們一點也不膽怯,不比高低,但要比個存在感。紫花地丁的名字好聽,我記得牢。
不過,小區葳蕤的野草,叫不上名字也沒關系,它們依然讓我親切而無陌生感,就如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突然憋住了喊不上名字,一聲“哎”,還不是表達了所有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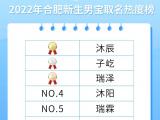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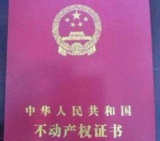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