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在老家買了一套三居室的樓房,給母親和小弟弟媳住。母親十分高興,她不住主臥,要住在有陽臺的那間。我知道,母親喜歡栽花種草。老家故宅院子里的花草都是母親侍弄的,現在有了樓房,陽臺就成了她的花園。
但是,陽臺的主要功用并不是栽花種草,而是她每年寒暑假、春節、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十一、元旦用來眺望我回家。只要到了我返家的日子,她就站在陽臺上,引頸遠眺。母親居住的樓是小區最南邊的一幢,是南邊東頭的一家。我只要從五六百米外轉過一片樹林,母親就一眼看出來是她的大兒子回來了。
我遠遠看見母親,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陽臺上隔著窗紗,站著一位銀發飄飄,面孔紅潤,慈眉善目,佇立遠望,頻頻招手,滿含笑意的老人,這是多么感人的畫面啊。每當我離去的時候,母親就站在陽臺上跟我招手送別。彼此都有些傷感和惆悵。一年八九次來回,看到老母親的形象,到家聞著陽臺上鮮花的馨香,撫摸著老母親操勞一輩子的雙手,開口喊一聲媽,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隨著歲月的流逝,母親一天天老了。八年前的一天,我離去時,母親倚門招手送我下樓。我家住二樓,下樓一轉過彎就是母親的樓下。以往母親送我出門,倚門再見,待我走到樓下,她就走到陽臺上,招手告別,這是她的常規。但是現在她步履蹣跚了,來不及走到陽臺,我就走遠了。但是我心有靈犀似地猛一回頭,母親居然踉踉蹌蹌地沖到陽臺,向我招手。我心里猛然一酸,她一定是不顧危險走到陽臺的。兒行千里母擔憂,三百來里也擔憂啊。她愛我,愛了幾十年,從疼愛到關愛,再到我也老了的惜愛。陽臺承載著母親綿綿無盡的深情。
2014年11月1日是母親99歲生日,按習俗百歲生日提前一年過。在生日慶典上,子孫四代親朋好友濟濟一堂,好不熱鬧。宴會廳外鞭炮齊鳴,廳內鼓樂高奏。母親身著金紅唐裝,接受眾人禮拜。老壽星懷抱鮮花,喜笑顏開,喝了好幾杯紅酒。緊接這一慶典是小弟的兒子研究生畢業,結婚,舉行盛大婚禮,母親大笑著接受孫子孫媳的跪拜和一大家子幾十口人的歡呼。接著老宅拆遷,開發商賠償的四套房子,母親分給了二弟、三弟、四弟和二妹。各家都辦了一個喬遷喜宴,請母親喝酒。誰知大喜之后,緊接著天大的打擊驟然而至,大姐去世了。這一變故讓母親痛不欲生,一連哭泣了幾天。我老伴說:老人大喜之后大痛,一般很難挺過去。
沒過幾天,二妹來電話,說母親經常昏睡,最愛去的陽臺也不去了。老伴說:“不好。老太太百歲大壽已過,一手帶大的小孫子已然成家立業,四個子女喬遷新居,老人家了無牽掛,她已無事可做。加上至親的親人去世,哀傷過度,她的陽氣耗盡了。”我一聽,心驚肉跳,決定回老家。第二天兒子開著車飛快地往老家趕。快到地方時,天下雨了,轉過小樹林,隔著雨霧遠遠看見母親正站在陽臺上。我對老伴說:“瞎操心,老太太不正在陽臺上嗎?”我滿心歡喜地憧憬著將要見到老母親的歡欣,兒媳從副駕駛位置上定睛一看,說:“那不是奶奶,是一件掛著的衣服。”我心頭一緊,情知不妙,車一停,我就快步上樓。誰知母親已經在我到來之前無疾而終了。
看著母親收拾得干干凈凈的陽臺,看到幾盆盛開的菊花、玉簪和君子蘭,覺得母親一生高潔如斯。我把菊花、玉簪和君子蘭搬來放在母親周圍,禁不住淚如雨下。
辦完喪事,返回合肥時,我回望母親的陽臺,仿佛母親還站在那兒,站在鮮花環繞的陽臺上。我欷歔不止,簌簌流淚,喃喃地說:“我沒有媽了……母親不在了,家也就沒有了,唯獨忘不了的是這一方陽臺。”
悲痛使我淚眼婆娑地寫下這樣的詩句:哀樂低回天淚雨,陽臺嗚咽泣英魂。人間最痛喪慈母,今世喊媽無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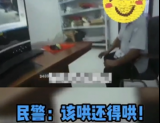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