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淮軍圩堡的理解,越來越接近于它們的內核。
肥西的三山(大潛山、周公山、紫蓬山),無疑是淮軍圩堡的密集地,張老圩、周老圩、劉老圩、羅壩圩、張新圩、蟠龍墩圩,如山中石拋向空中,落地生根,在時間的縫隙里歷久彌堅,和山一樣堅挺。
“莫犯三山”,是太平軍短暫的歷史中,面對群山眾巒發出的不多驚呼。大音希聲,卻又驚心動魄,鑄就了一方山水土木的驕狂。圍三山嘯起的淮軍,以人的名號立威,樹字營、盛字營、銘字營,步步扎營,雖無堡壘之名,卻有穩健鎖固之實。
建立圩堡式的家園,是在眾淮軍將領功成名就,三山從激蕩中歸于平靜之后。圩堡以三山之石為基,參天巨木為椽,山水地氣為壕,一統于山的敦厚、人的樸實。
每個圩堡都住著一位頂天立地的漢子,都住著一些傳奇,甚至住著金戈鐵馬后,一汪無盡的溫柔。
張老圩和兩廣總督張樹聲聯系在一起,而之后的張家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充和、張兆和,流動出如水的斯文,讓張老圩在歲月的破敗里,時而發出翠綠的新枝。
劉老圩和劉銘傳結緣,臺灣首任巡撫以樹的名義駐扎,成為大潛山最具特色的一棵。圩堡用遺落的盤亭和讀書島訴說,叱咤風云原本有溫存、柔和的一面,詩書耕讀,才是圩堡人的本質。
不一而足,圩堡的故事陳舊卻又新鮮。
我常在三山的圩堡里放縱目光,目光常被歲月擊碎的瓦礫、颶風吹折的大樹打斷。我也常聽到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一聲聲嘆息如蟲子躲在旮旯里振翅般,那么的無奈,那么的不可拾取。
從山的封存里走出,又重新建起狹窄的天地來,圩堡確實是思想的符號。劉銘傳們終沒脫離封閉的窠臼,只是反復聽取山風的狂烈,伴之以自己的呼嘯,而從沒想過,驟然于一場暴雨,摧枯拉朽,滌蕩出一個新世界。作為一個百年后的老鄉,我常為之抱憾。
實際上圩堡的主人,多是有世界眼光,比如劉銘傳,在主政臺灣后,建郵局、修鐵路、興學校,讓一塊蠻荒之地,透出無限的生機,被稱為“臺灣近代化之父”。甚至在他筑建的劉老圩——大潛山房,修建了西洋樓,中西合璧,足足地堪稱西洋景。
研究淮軍,繞不過淮軍圩堡。圩堡中沉淀了太多的淮軍元素,它們是一個博大的容器,盛裝著搓揉不透的零碎而又是一個恢弘的整體。
總以為淮軍離我們很遠,更多的時候卻因圩堡,淮軍和我們貼近。我的一個遠房叔叔,他的爺爺曾經是淮軍的一員,隨張樹聲征戰,后落腳于天津衛,種下了小站稻之類。
叔叔尋根問祖,循著淮軍圩堡而來,最終找到了故鄉。當叔叔在老祖宗的墳前跪下雙膝,將頭叩在厚重的黃土地上時,他了卻了幾代人的心愿。歸根,根可扎得更深。
叔叔歸來,鄉人用純凈的大米為他接風,他吃了一碗又一碗,嘖嘖稱贊,和小站稻有同樣的香味。接著改口,小站稻擁有故土大米的香氣。一百多年的鄉愁,在圩堡的呼應下,得以落地。
我有幸隨作家們一起,尋訪淮河源頭,在淮陽,我發現了淮軍的蛛絲馬跡。淮軍為何奔赴淮陽,我不想深究。當我明明白白地知道,劉銘傳打馬在淮陽的土地上狂奔時,心跳猛地加劇,我陡然間想到了劉老圩。劉老圩,在流逝的時光面前,靜而又靜,似乎再也不會有漣漪泛起。
探源歸來,我去了劉老圩,我想告知省三先生,我走了他曾走過的一段路。圩堡無聲,一臉大麻子的劉銘傳無聲,倒是他的一首《淮陽夜泊》在大聲回答:“淺灘舟泊處,徹夜水流聲。風浪今無險,漁燈漸有明。”劍戈入庫時,方有詩情。劉老圩中可作詩,而詩自在圩之外。
圩堡在發散,即便圩堡陷于歲月,沉淪于歲月,但它傳遞的文化氣息仍可時時感受。
不僅僅是三山,在肥西的土地上,淮軍圩堡隨處可尋訪,唐五坊圩、葉大圩、董小圩等等,組成了獨具特色的圩堡群,其規模其聲勢、其包含的文化符號,都是不可復制,更不會再生的。
對淮軍圩堡的理解真的很難,我把目光看得更遠些。擁有淮軍圩堡群的土地,自商周以來,就聳起了一些土墩,或城池或烽火臺或村落,它們和淮軍圩堡一樣,難以被讀透。但我以為,這絕不僅僅是為了標新立異,炫耀一種風彩。
我徹悟過,墩和圩堡的重要設定,肯定是為了安全。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淮軍圩堡帶來了安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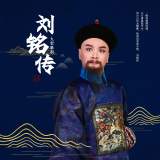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