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那幢小樓,已消失好些年了,但它時常會來我夢里。
剛結婚那會兒,住在學校。當時,校園里只有一幢比較像樣的教師宿舍,就是這小樓。小樓兩層,上下各五戶。門前有長長的內走廊。樓梯是從二樓中間那戶門前開始,呈“7”字形延伸至地面。
當時,樓里住的都是小夫妻倆帶一孩子。人口最多最熱鬧的一戶是丁老師家。婆婆住她家,她大伯子小姑子經常帶著孩子來看老人。房子小,孩子們就在走廊上來來回回地跑,她小姑子就站外面看著。丁老師在屋里樂呵呵地炒菜做飯。她身材嬌小,嗓門卻很亮,從來都是不笑不說話。我一直挺佩服她:那么一大家子人,她總是應對得妥妥帖帖。
每到飯點,我們鮮少規規矩矩圍桌而坐,總聚到走廊上,在丁老師家門口的時候居多。大家端著碗,互相瞅瞅,不嫌棄的還從對方碗里搛兩筷子。我素喜捧大碗吃飯,菜總是堆得高高的。愛開玩笑的趙老師常說:喲,看著你蠻瘦弱,沒想到這么能吃啊!久而久之,我就得了個響亮的“雅號”:某某學校最能吃的女教師。
樓里住的女教師都比我大,比我有生活經驗。她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朱老師擅針織、縫紉,我跟她學會了鉤墊子、織毛衣。她還教我做過兩條孕婦裙。盛老師愛晾曬,一有太陽她就忙不迭地搬被子出來。她叫我也要多曬,防濕氣。樓下的徐老師套被套時有時會叫我幫忙,幾次下來,我自然學會了。
樓下的俞老師,烹飪技術在我們學校是出了名的好。她教我做過兩道菜,我印象特深。一個是“臭干子煲”。把臭干子切成三角形,下鍋煎至表面略黃,撈起冷卻;再在干子切面劃道口子,塞入剁好的肉泥;最后,與冬筍等配料入鍋同煮。另一道是湯。排骨加山藥、木耳、玉米入鍋同燉,湯成,白、黑、黃色彩豐艷;吸溜一口,醇香有味,濃而不膩。俞老師不僅菜做得好,還會做餅子、粽子、南瓜圓子等各種吃食。每次她總是亮著大嗓門站門口喊:你們想吃的就來啊!后來,俞老師買房搬走了,我家小子還常念叨:唉,現在不跟夢澤(俞老師兒子)家住一起了,沒好吃的了!
小子是在我住進樓里第二年出生的。當時樓里的孩子盛老師家飛飛最大,被孩子們尊為“孟大王”。小子能走路以后,只要“孟大王”一招手,他就和聰聰(丁老師女兒)、夢澤幾個一起,屁顛屁顛地跟在飛飛后面,在校園里到處跑。或到操場的沙坑邊玩沙子,或在樓里“躲貓貓”,再不就是比賽騎小三輪車……吃飯時,我們幾個媽媽派一人下樓找,把汗流浹背的小家伙們一并領回。
那時,學校供電情況不好,晚上經常停電,大家就聚到走廊上,聊天說笑。男的湊一堆,點著煙,聊時事談球賽;幾個女人圍一起,說孩子怎么怎么淘氣,又有哪些衣服好看。小家伙們自然是靜不下來,在走廊上咚咚咚地跑過來跑過去,好在有月光照著,也不會摔跤。白天上班,我們也從不鎖門,只虛掩著或直接大門洞開,反正大家課不同,樓上總不斷人。大凡誰家買了啥新鮮物件,總要在樓道上先展示一番,才進家門。獲得展示機會最多的,自然是我們女士的新衣服。偶爾哪家兩口子拌嘴鬧出了動靜,大家也都會去勸解。男的拉男的,女的勸女的,角色對應很鮮明,不一會兒就成功“滅火”了。
后來,朱老師全家搬去了南京,徐老師去縣城住了,張老師也調走了。再后來,我們搬進了縣城的宿舍樓。住新房雖然興奮,卻也感到不適:一進家,防盜門就砰地關上了,再不能像從前那般端著飯碗東串西串,買了新衣服也沒人在旁邊品評討論了,孩子也失去了玩伴……
而今,多年已過。我們早已習慣了進門關門、從不串門的生活模式。同一小區的住戶,互不相識者比比皆是。我家對門幾易其主,我至今不知戶主何人。可當年小樓生活的場景,仍歷歷在目。前些年學校擴建停車場,小樓已被拆了。我每次看到那位置,心里總會泛起溫馨的漣漪。那段溫暖純真的歲月,深深鐫刻在記憶的底片上,永不褪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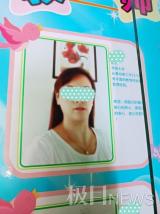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