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訊 安徽省藝術研究院院長、書記、安徽省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新戲劇》主編李春榮,日前應邀做客由古井貢酒年份原漿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欄目,李春榮結合自己在安徽省藝術研究院30多年的工作經歷,真誠致敬安徽藝術創作研究的“輝煌時代”,坦率直言今天的現狀,展望安徽藝術研究未來的走向。本期節目已于9日上午10點在安徽網、大皖新聞客戶端正式上線。

省藝術研究院的前世今生
仰望安徽戲曲“黃金時代”
徽派:安徽省藝術研究院,研究是實驗的科學的,藝術又是主觀的。那么安徽省藝術研究院的職能和定位是什么呢?
李春榮:安徽省藝術研究院是省文化和旅游廳下屬的二級單位,是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最早可上溯到上世紀50年代初安徽省文化局的文藝創作室和音舞工作室。
我們通常意義上講的安徽省藝術研究院,是1978年2月份,通過省編辦下文成立一個安徽省文藝創作研究室,第二年改名正式成立安徽省文學藝術研究所,這也就是后來人經常說的“文研所”時期。成立時,將當時省內的文學藝術各行的大家、專家集中在一起,就是我們講的“掐尖兒”,集中到“文研所”,比如像著名編劇、理論家陸洪非、金芝、完藝舟、作曲家時白林、美學家郭因,等等。當時被戲稱為文化廳的“翰林院”,當年廳里評職稱,我們所里的專家評委往往占一大半。后來文學分開歸省社科院了,我們變成安徽省藝術研究所,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藝研所”。
1983年的時候,省編辦又給我們一個職能,就是安徽省劇目工作室,承擔全省的戲劇創作及管理工作,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進入新千年之后,重新規劃調整,“安徽省劇目工作室”這塊牌子去掉了,但是我們還自覺承擔這個一部分職能。2008年我們將“所”改成“院”,這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藝研院”。
徽派:聽起來是一個非常長的歷史沿革。
李春榮: 2013年安徽省文化廳又給我們掛了一塊“安徽省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牌子,主要承擔全省的藝術科研,也就是藝術學課題的申報及日常管理。所以說省藝術研究院的職能就是藝術主要是戲劇研究、創作加上相關的人才培養。
徽派:要干的事情還挺多,隨著時代的變化一直在變化。剛才提到“黃金時代”的時候,都是耳熟能詳的名字,聽您說到“翰林院”的時候,有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李春榮:“黃金時代”我沒趕上,我對那個時代是仰視的。1990年我大學畢業分配過來,老先生們還都在崗位上,盡管當時他們從年齡上都該退休了,但是很多六七十歲的還返聘在工作,我進單位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在《安徽新戲》編輯部,當時這個編輯部有十三個人,時年六十多歲的金全才先生(人們更熟悉他的筆名金芝)當時是藝研所的副所長兼《安徽新戲》主編。
編輯部里有70多歲的,有60多歲的,像最早一版的黃梅戲《天仙配》的導演李力平就在編輯部當編輯,他喊60多歲的曹野先生“小曹”;還有5、60年代安徽話劇界著名的李培仁導演;50年代北大王力先生的研究生孫寶琳老師,他們都在當編輯,那是很令人懷念的年代。
徽派:大學剛畢業分到編輯部,編輯部有哪些故事是值得我們書寫的。
李春榮:當時我們一個省藝研所就有三份雜志,其中一個《藝譚》雜志當年在全國文藝理論界非常有名,很多大家以及后來的大家都在這里發表文章。當時《安徽新戲》上發表一個戲,無論你是農民還是無業,馬上可以轉為吃商品糧的國家干部,毫不夸張的說,《安徽新戲》培養了整個安徽大部分的編劇人才。那時候寫戲的人很少受過專業訓練和教育,編輯部的老先生、老專家們帶著自己的熱情,自己坐著公交車到下面縣城或鄉下,去跟作者交流,可以講是手把手教,后來活躍在安徽劇壇上的一批當年的青年編劇都深受教益。比如當時和縣一個回鄉青年寫了一個劇本,經編輯輔導后在《安徽新戲》發表了,省話排演后就把他轉正招干到了縣文化館成了國家干部。還有淮北的個體戶、徽州的農民,等等,都是通過發表了劇本以后招干到了文化創作部門。
當年我們每個縣都有創作人員,都有拿得出手的編劇人才,的確跟社會大環境有關,跟老專家、老藝術家的奉獻精神有關。但是我們院里現在連一份正式的專業刊物都沒有了。
徽派:現在找不到專業期刊,碰不到伯樂。
李春榮:今天有今天的時代和環境,我們的職能也變了。

專業學習打牢藝術基礎
工作崗位歷練雜家本色
徽派:您在這里,從1990年到現在,經歷了起起伏伏,看到各種變化,也有遺憾的部分。
李春榮:前面都是大家、專家,鋪墊得太高了,我們院獲得國務院津貼的有13個專家。在我們那個很破的樓上,我上任后做了個成果展示,從1樓上來,一直到6樓,當年的藝研所也好,現在的藝研院也好,所有的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專家的照片都展示出來,那確實很輝煌。
徽派:從您個人來說,見證了從研究所到研究院,改革新生的狀態。您開始是搞創作的,也在不停變化和改變,作為創作者的理念有變化嗎?
李春榮:我當年在上海戲劇學院讀的是戲劇文學系,但我學的是戲劇理論專業,是我們上戲戲文系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屆戲劇理論本科班。學校原本是按師資后備力量培養的,所以很下功夫,回過頭看當時給我們上課的都是大師,像戲文系的陳多、余秋雨、丁羅男、葉長海這些老師,表演系的陳加林老師,導演系的張仲年老師,舞美系的金長烈、周本義老師,等等。教音樂欣賞的是劉如曾老師,就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那段音樂的作者。
說實話,當時我們很少接觸戲曲,盡管現在上戲有專門的戲曲學院,但當時沒有,我們在學校時學的是話劇和影視,所以,我到單位以后傻眼了,我們安徽省藝術研究所主要是搞戲曲。
徽派:安徽戲曲確實是一大名片。
李春榮:隨著我們單位老專家、老同志退休以后,一下出現了人才斷檔,接不上了。后來改革,事業單位逢進必考,能考進來的人都是碩士,學歷很高,基本是學文藝理論的、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的,進單位前基本沒寫過戲,甚至有的都沒在劇場看過戲,戲劇學院畢業的都很少。就連我們院里職工子弟考到上戲、中戲的畢業后都沒有一個回來的,這其中原因很復雜。
徽派:這里面確實存在一些問題。
李春榮:文旅部科教司現在在統計各省藝術研究院所的職能,一個是做藝術研究,一個是藝術檔案,還有非遺研究,現在文旅融合還有旅游研究,還有一部分是藝研院所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創作功能。雖然我們院現在沒有劇目創作室或者創作中心這個牌子,但是牌子沒了,職能也要有,有實無名,我們也要做。這批考進來的年輕人都是研究型人才,必須要轉,要雙肩挑,藝術創作和藝術科研都要搞。
省級藝術研究院每個人都應該是多面手,就不能像國字號或高校那樣高精尖,我們這里就是雜食動物,要做雜家。所以你看我經歷里什么都有,什么都要參與,這是一個過程。


藝術科研要聯系藝術創作實踐
藝研院要做藝術創新開路先鋒
徽派:藝術研究和藝術創作確實應該也是相輔相成的。
李春榮:我們省藝術研究院過去主要就是搞戲,在全國我們的黃梅戲創作研究是走在前列的,尤其是黃梅戲音樂創作和黃梅戲研究。從時白林老師到徐志遠老師,就著這樣的條件,我們辦了好幾期國家藝術基金的人才培養項目,第一個項目就是黃梅戲作曲人才培養,一下在全國招了20幾個學員,我在開班儀式上講,如果我們這個班能走出一到兩個徐志遠老師這樣的黃梅戲作曲家,我們的黃梅戲就還能再繁榮幾十年。
我當時和徐志遠老師去北京進行項目答辯,我們講了幾句話就出來了,評委們無可爭辯,一致同意。我講黃梅戲好聽好看,廣受歡迎,但是現在黃梅戲最大的危機不是缺乏演員,也不是別的,是缺少作曲,一個劇種最大的特色體現在劇種音樂上。
徽派:確實戲曲的唱腔是一個曲種的典型特征。
李春榮:以前我也反映過,戲曲搞非遺傳承人都評演員,其實最該評作曲,當年我們準備報時老去評首批非遺傳承人,但是規定是研究者不能做非遺傳承人。其實戲曲劇種的區別在音樂,你只有把音樂一亮,才知道這是唱什么戲,否則你把音樂一關,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戲。
在北京答辯時我說,黃梅戲最緊缺的人才是作曲家,在我身邊的這位徐志遠老師是目前還在創作的最年輕的黃梅戲作曲家,但是他今年已經退休了,再過若干年,等這批老同志退出了就沒有作曲了,沒有作曲你還唱什么戲?后來我們又做了廬劇作曲人才培訓班,都大獲好評,這幾年已經見到成效了。我們還給湖北培養了一個黃梅戲青年作曲人才,現在他很火。現在我們省內做戲曲音樂創作的新人基本全部是我們那兩個班培養出來的,我覺得這是我們省藝術研究院應該做的,我們不僅要培養本院的青年人才,還要發揮優勢,培養全省甚至相關重點劇種的藝術人才。
后來我們又辦了全國地方戲青年評論人才培養班,把全國12個省做戲曲評論的青年人才,包括高校的都匯聚一堂。今年省委宣傳部搞的安徽省建黨一百周年優秀新創劇目展演,把評論任務就交給了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戲劇專業委員會,作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戲劇專業委員會主任,我帶領以我們院和省直單位青年專業人員為主,以及我們上次那個評論班在合肥地區各高校的青年教師一起做這個評論,收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
徽派:其實您看這個問題的視野還是很開闊的。
李春榮:單位的年輕人是要培養,更要面向全省,你這個單位有什么價值,價值就在這,在你這個行業做領頭羊。前幾年我們做了一個實驗劇黃梅戲清唱劇《漢宮秋》,新聞發布會上我就講,我們藝術研究院的人才,過去是擰在別人的機器上,這次要組裝一個我們自己的機器。
我們為什么要做這個劇?當時梅花獎演員周源源調到我們單位,我們就想給她量身打造一個作品,但又不想做一個一般的作品。這個清唱劇就周源源和黃新德兩個主要演員,整部戲一共就四個演員,另外兩個演員是省黃的丁普生和陳丹,加上一個合唱隊,還有樂隊也上臺了,我們參加了安徽省第二屆文化惠民演出,放在最后一場,壓軸。
徽派:這是一次創新和嘗試,后來效果應該很好。
李春榮:演出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惠民演出票十塊錢一張被劇院門口的黃牛炒到一百塊,劇場里還加了2排座位,爆滿。這個充分說明了戲曲創新的力量。就像我在新聞發布會上說的,我們藝術研究院為什么要從后臺走到前臺,是因為藝術。
科研要聯系藝術創作實踐,藝術科研成果要轉化為產品面向實踐。清唱劇放大黃梅戲唱腔優美的特長,以明星領銜,簡單的道具,合唱隊和樂隊上臺,場面也是很好看的,我們是給專業院團開路的,我們在前面滾地雷陣,我們做實驗,專業院團可以跟進,可以吸取經驗和教訓。后來省黃和安慶也做了清唱劇和小劇場戲,效果不錯。
徽派:打了一個樣板。這也是藝術研究院的職能。
李春榮:對,我們做實驗,我們如果成功了,大家就能從里面看到希望,我們如果做失敗了,他們也可以吸取我們的教訓。安慶在小劇場這一塊做的非常成功,已經成了他們的一個品牌,這其中離不開黃新德。黃老師作為黃梅戲清唱劇《漢宮秋》的主演和藝術總監,他到處跟人宣傳這個戲形式蠻好的,包括徐志遠老師,雖然沒有參加這個項目,但是首演他看了很激動,也是到處去宣傳。
我覺得從這點說,戲曲藝術必須要創新,怎么創,不是瞎創,作為專職藝術研究單位就應該多做這方面的實踐。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時代需要我們必須要改革,必須要創新,必須要轉型,不轉不行了,現實倒逼你了。下一步我們研究院怎么辦?那就是,圍繞安徽文化藝術發展這個中心,服務全省藝術創作研究大局,發揚優勢,守正創新,培養一批有影響的藝術創作研究人才,為安徽文化強省建設做出應有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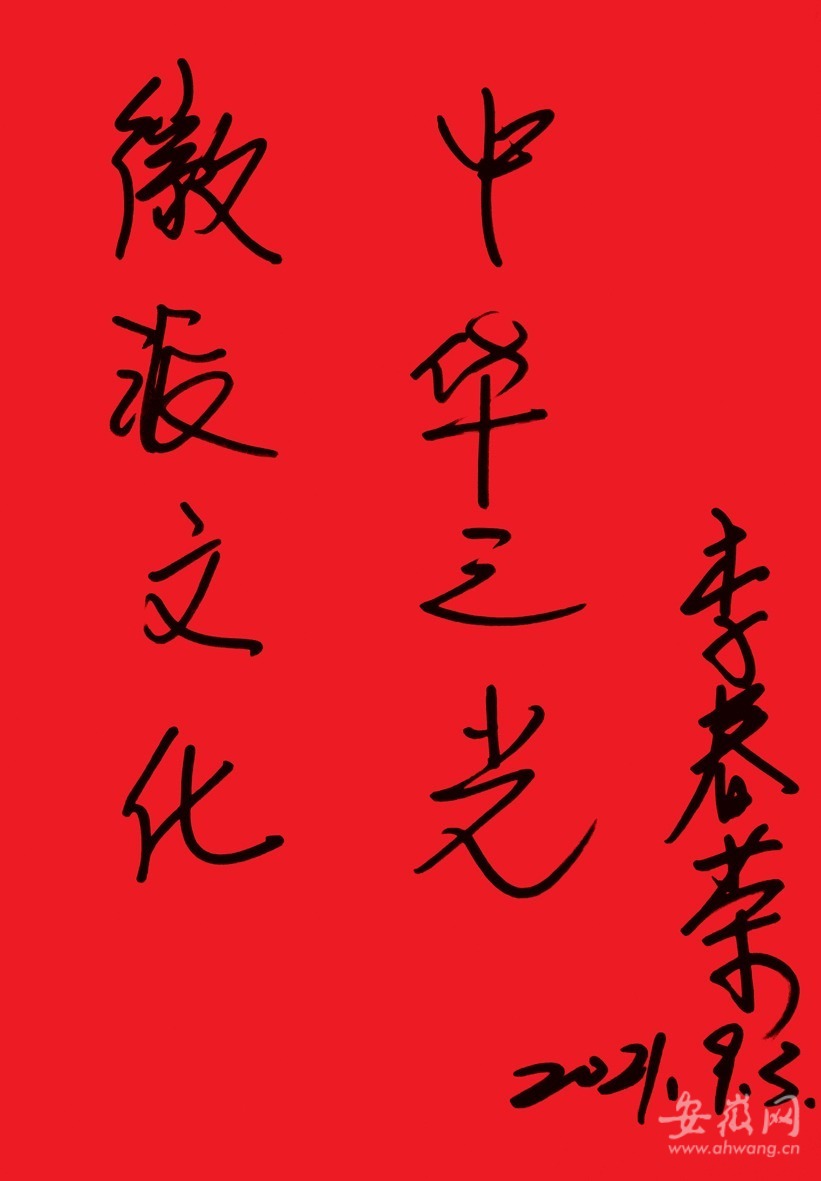
藝術研究和創作雙輪驅動
行政和業務努力找平衡點
徽派:院長說了特別重要的一個問題,我發現您非常推崇研究不能是無根之水,不能是空中樓閣。我很好奇,作為一個藝術創研單位的領導者,同時又是專業人員,您是如何協調這兩個身份的?
李春榮:再有幾年時間我就要退休了,回頭想想,盡管做了一些創作,但是沒有什么優秀作品,沒有什么大作品,可能和我“雜食”有關。我們省級藝術研究院,必須要雜,叫你寫個晚會主持詞你要寫,叫你寫一個通訊報道也要能寫,叫你寫一個調研報告你也要寫。我們搞的《安徽小劇種生存和藝術生產狀況》調研報告去年獲得文旅部全國文化和旅游系統2019年度20佳調研報告,全國300多個我們拿了全國第14名。
2018年我作為首席專家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中國70年戲曲史?安徽卷》獲批,成為安徽省第一個拿到的藝術學重大項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二個。在全國省級藝術研究院所我們也是第一個拿到藝術學重大項目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是國家級藝術研究的最高資助項目,拿到非常不容易。自2011年我上任院長之后,除了重大項目之外,我們還分別拿到了藝術學青年項目、文化部智庫項目、文化藝術研究項目,今年我們又拿到了藝術學一般項目。作為省藝術研究院,我們責無旁貸,應該挑這個頭。作為省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今后我們要加大宣傳,尤其是加大對高校的宣傳力度,希望我省有更多的高校、更多的老師加入到藝術科研的隊伍當中。
徽派:您的關注點更大了。
李春榮:但是,藝術創作的功能不能丟。過去輝煌的年代每個縣都有一兩個像樣的編劇,現在一個市都難得有一個像樣的編劇,這就是差別。過去像安慶、像宣城,當年還有“宣城現象”,都有叫得響的編劇,現在全省的藝術創研室這個系統幾乎名存實亡,許多市的創研室都不進新人,自生自滅;要么就是拿去給不好安排編制的人掛在這個地方,雖然有創研室但是沒有真正搞創作、研究的人。面對這個問題,作為全省藝術創作研究的龍頭單位,我們不僅要做好自己的事,也要帶領全省藝術創研系統走出困境。作為我個人,雖然也承擔專業工作,更多的,首先是院長和書記,要做好黨務和行政工作,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這個是必須的職責。
徽派:感謝李院長分享的這波內容,讓我們明晰了安徽省藝術研究院的職能和定位,開拓了我對它的認知。從歷史看,李院長把省藝術研究院的職能是開拓了的。我最大的感受是誰說女子不如男?還有一個感受是,雜家也能成大家。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文 薛重廉攝
編輯:陶娜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