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長一段時間,我是不太愿意把合肥認(rèn)作我的故鄉(xiāng)的。
少年時代遇到初識的朋友,人家問起家鄉(xiāng),我總要不厭其煩地解釋,在安徽省六安市下屬的一個小縣城底下,有一處叫梅山的小鎮(zhèn),那里是我的家鄉(xiāng)。旁人聽得一臉模糊,我才退而求其次道:合肥,合肥知道吧,我家后來搬去了合肥。
要怎么解釋那其中別扭的少女心事呢?對于一個青春期的文藝少年而言,合肥這兩個字來得太直白,太突兀,太不詩情畫意。這里的空氣似乎太干燥,噪音似乎太嘈雜,方言也似乎——不太好聽。
我是喜歡各種方言的,有的語系譬如粵語或者江浙方言,全然將你隔絕在外,抑揚頓挫之中獨自演繹一套繁花似錦,有的語系將你囊括在內(nèi),比如東北話和四川話,不問來歷就興致勃勃兜攬你融入其中。而合肥話——要我怎么說呢,在似懂非懂之間異化了音素,夸張了語調(diào)又模糊了細(xì)節(jié),有時候只言片語,便大剌剌營造出難登大雅之堂的土氣效果。
總之我來自距離合肥兩小時車程的一個小鎮(zhèn),8歲時隨父母遷來省會,花了大約兩年習(xí)慣這里的生活,花了大約五年習(xí)慣這里的聲音,直到高中,我才漸漸和大家一起,笑著聽班上的男生用合肥話唱一些滑稽歌曲。
而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因為唱歌的男生長得不算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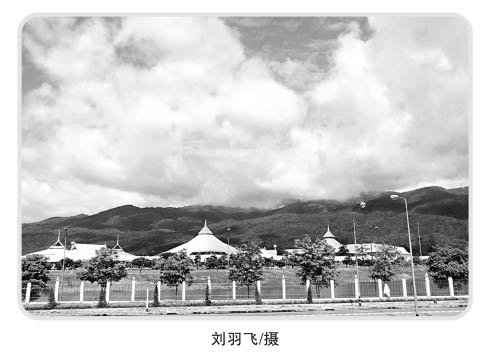
二
大學(xué)畢業(yè),我堅決拒了保研,打定主意要去遠(yuǎn)方開啟下一程人生。于是22歲那年的夏天,我終于告別了這座生活了14年的城市,考去廈門,在南方度過了最為愜意的三年。初到的時候自然言語不通,但三年之后,我不僅有些喜歡上閩南語的婉轉(zhuǎn)吟哦,甚至能從巷口攤子后阿嬤的召喚中聽出幾分親切來。
再后來我研究生畢業(yè),進(jìn)了浙江一所高校當(dāng)起老師,某年新學(xué)期第一節(jié)課下課,有學(xué)生興沖沖地過來問:"老師,你是哪里人?"
"安徽。"
"安徽哪里?"學(xué)生更興奮了。
"安徽——安徽合肥吧。"我想了想,決定采用簡化版。
"我就知道!"學(xué)生比了個耶。
"我的口音有那么明顯?"我有些詫異,一面暗暗反思到底是哪里暴露了。
"個別詞我能聽出來哈哈哈。"老鄉(xiāng)廝認(rèn)完畢,學(xué)生笑嘻嘻地跑開了。
我甩甩頭,決定在下一節(jié)課把每個音都拗得更加字正腔圓一些。
三
很多年后我和幾位新結(jié)識的本地朋友出游,有一次去湖州,回來路上車子經(jīng)過一個叫"織里"的小鎮(zhèn),同行的雞哥望著路牌開始長吁短嘆,覺得這里才應(yīng)該是他的家鄉(xiāng)。雞哥是標(biāo)準(zhǔn)的讀書人和文藝青年,文藝水準(zhǔn)達(dá)到了周圍一眾朋友可以對旁邊的人說"我有個詩人朋友"而不覺得羞愧的地步。一片轟笑聲中,我似乎忽然同那個年少別扭的自己握手言和。
一天下課收到老友短信。
"暑假回去么?有點懷念合肥了。"
怎么會不懷念呢?那些綠樹陰濃的漫長夏日,太陽把臉曬得通紅,彼時還不知防曬為何物。知了叫個不停,我們一頭栽進(jìn)新華書店,一邊蹭空調(diào)一邊在書中廝磨一個下午的恩怨情仇,傍晚出了門,在三孝口或者四牌樓的某個路口買一杯甜粥或是幾根炸串,就著晚風(fēng)順便把一個學(xué)期的八卦從頭到尾聊一遍。冬天里手凍得通紅,和好友放學(xué)一起走到半路,忽然都想吃烤紅薯,掏出五毛錢買一個,選來選去選了個瘦長條的,皮已經(jīng)烤得焦脆,輕輕一撕就露出里面的紅瓤,上面還泛著一層糖油。
更多的時候,是放學(xué)早早到家,趁著爸媽還沒回來火速切換到電視劇頻道,從新白娘子傳奇看到東京愛情故事,從壹號皇庭看到鑒證實錄,從神雕俠侶看到天龍八部,忽然聽到樓梯間腳步聲響,立刻彈跳起身,飛速將電視鎖定回新聞頻道關(guān)掉,伴隨著門口鑰匙響動,自己已經(jīng)安然坐回書桌,正襟危坐地在寫作業(yè)了。
怎么會不懷念呢?
今年春天女兒開始學(xué)鋼琴,小湯第一冊里有首曲子叫《打電話》。
"兩個小娃娃呀,正在打電話呀,喂喂喂,你在哪里呀?哎哎哎,我在幼兒園。"
聽著聽著,眼睛忽然有些濕潤。
記得安電話的那一年,我八九歲,才剛搬去合肥。市內(nèi)電話費是一毛錢一分鐘,長途好像是三毛錢,打得多了媽媽會念叨。
盡管如此,每天放學(xué)還是忍不住想打,想打給梅山的外公外婆,想打給放學(xué)路上剛剛才說再見的好朋友。
喂喂喂,你在哪里呀?哎哎哎,我在合肥呀。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