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我的身份證核發日期是1986年12月31日。照相那天,居委會一紙告示,招來一列長隊。矮墻上掛塊淡色布,前邊放張方凳,方凳前的三角架上,固定著一臺小小的相機。此屬第一代身份證,不收費。任憑你長龍隊伍嘰嘰喳喳,嘻嘻哈哈,條桌前的工作人員都不為所動,驗好一個,放行,“咔嚓”一下,再放下一個。他們深知,此刻任何細微的疏忽,都可能使全盤亂套,甚至釀成前功盡棄的可怕后果。
我的身份證拿到手,妻子夸張地說:“我的媽呀……”我說:“這就對了,這才是本色的我。無論是你,是我,是明星,還是其他什么人,要的都是這種正面大頭照,任何施脂抹粉、騷首弄姿、裝模作樣,都不能上身份證。”
第一代身份證全是手工操作。面對身份證,我慨嘆:真佩服居委會、派出所,成千成萬的“卡片”哪,短期內,他們是從哪里找來那么多心細的寫字高手,把每張身份證寫得那么精準,那么漂亮!
我首次使用身份證是在1987年年底。單位主要領導赴北京參加一個全國性會議,我是隨員。機票是行政科事先訂好并分別交給領導和我的。登機驗票時,領導因忘帶身份證,而被驗票人員攔了下來。飛機不是小車,它不等人。領導讓我先走,他在機場改乘下一趟航班。合肥當時還沒有飛北京的直航,下趟航班要等半夜從上海飛來再轉飛北京的加班飛機。真得謝謝上海的這趟加班機,不然,全國這么重要的會議,我單位的領導卻遲到,這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事后,有人對我說:“當秘書的,領導想到的,你得想到;領導沒有想到的,你也得想到。”很明顯,我不是一個合格的秘書。
我的首張身份證,期限是20年。我還沒有怎么使用,它就到期了。當時,我才真正感受到,“白駒過隙”是多么的緊迫、無情和殘酷!我的第二張身份證是2003年4月8日更換核發的。這次是“個人行動”,自己到指定地點去照相,依規收費。身份證還屬第一代系列,文字不再是手寫,而是改用電腦敲定,有效期是“長期”。第一張身份證剪去一角后,留給我作紀念。兩證兩相對照,妻子又取笑道:“這是老子,這是兒子!”過去在家鄉,二十年一代人、四十歲當爺爺,是常事,這回,我卻有點忌諱了。我說:“別那么夸張了!兄弟倆還差不多,這張是大哥,這張是小弟。”
科技的迅疾發展和應用,有時是超過人的想象的。才幾年工夫,我的那張具有永久性質的身份證,便難以“長期”下去,需要換成帶有智能芯片的第二代身份證了。這次更方便,到所屬派出所辦理就行。這次是彩色數碼照片,我的大頭照一下子精神亮麗了許多。我一次沖印了大小幾十張,此后的乘車卡、老年證、社保卡,用的全是這張照片。只可惜,這張漂亮精致的身份證,我幾乎沒有怎么使用,它就不見了蹤影,棄我而去。我只得申請掛失、補辦。
補辦是在辦事大廳進行的。主事者還極人性化地先給我辦了一張臨時身份證,使我沒有失“證”的感覺,更少了種種因失證而帶來的麻煩。只是2019年的我,已今非昔比,皺紋滿面,寸發不存,丑陋得都有點對不起自己了。與第一張身份證上的照片相比,妻子說:這張是“爺爺”,這張是“孫子”。我無言以對,不再爭辯。
我身份證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在最近幾年。每當我快速報出身份證號碼時,白衣小姐都投來敬佩的目光,并相互議論說:這老頭真厲害,記憶力超強!其實,我是玩了一點小機巧,只要熟記編碼排列規律,誰都能夠做得到。不過,聽到他人對自己的夸贊,我還是有點暗自得意,像個小孩,挺享受的。
我的生日,農歷的,母親記得,妻子記得;公歷的,兒女們記得;唯獨我自己,總是不記得。有了身份證,再加上智能手機,“旁人”比家人記得還準確,每到那一天,短信祝賀之辭,突然集中出現,讓我驚喜不已!
我曾先后擁有5張身份證。歲月留痕。我的人生密碼,差不多都隱藏在這些小小的卡片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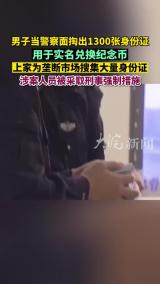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