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我在哀傷的氛圍中冥想,我在記憶的長河里追尋——安徽文壇才華橫溢的老作家、合肥本土滿身掌故的好鄉賢,一年多前以九九遐齡駕鶴仙去,能不憶彭拜!
從正心巷到二里街,80年一路“寫”來。論年齡,彭拜長我父母一兩歲,是長輩;論知識,彭拜滿腹經綸,我充其量只能算后學。自打結識,我學到很多,真的很澎湃。
彭拜的人品很澎湃。記得初次投府拜訪是38年前,受供職單位指派,為一部合肥籍名人書稿,請他把關潤色。那時他“復出”不久,剛搬進省文聯宿舍“文園”,三室一廳,在迭經坎坷30年后,終于有了自己的書房兼會客室。他說他深知老之將至,文思泉涌,筆耕不輟。書一本本推出,南方和本省的幾家出版社還不停地“催債”,但他都一口應允,為摯愛的家鄉和合肥名人做“無償勞動”。如劉銘傳詩所云,“圈圈點點又叉叉”,幾次三番下來,我們的書“增光添彩”了,可他的書耽擱了,只能熬夜在“補蹉跎齋”里“惡補”。我忐忑不安,他卻說很高興結了個“忘年交”,送我的書題上“友誼之樹長青”,還說請“方家哂正”,我受之惶然有愧。彭拜是“老合肥”,知道我研究地方史,給我提供了不少親見親聞親歷之掌故,我把它們收入《合肥文史資料全書》中。可后來有一段時間,他卻一再婉拒我上門請安,說“老相”不中看了,我也就沒再堅持,誰料想竟成永訣!
彭拜的作品很澎湃。他可謂“全才”,拿手的小說之外,散文隨筆、詩詞聯賦、劇本歌謠,樣樣擅長。中國作家網介紹:著有長篇小說《漢苑血碑》《紅顏幽夢繞香山》《斜陽夢》《梨花夢》,中短篇小說集《驕傲》《搬家》《潮州夢》《清淚沉江》,文集《婚后之戀》,舊體詩集《舊夢小集》《回音壁》,劇本《幸福》等,小說《三人行》《李馬渡康王》被選入多種選本,散文《婚后之戀》收入《中國散文精品·當代卷》等20種書刊。進入新世紀,又有小說《遠夢殘痕》等出版。《斜陽夢》1990年由漓江出版社推出,雖是老合肥的市井畫卷,卻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舒蕪、魯彥周、公劉、劉祖慈、沈敏特、嚴陣、柯文輝、段儒東、韓瀚等名家力挺。即使有“對號入座”,有爭議,也收到“洛陽紙貴”的效果;《婚后之戀》把“我”與“她”新婚之夜“解懷”后寬衣,帽子和耳環誰壓在誰之上,喻示今后誰能壓住誰,寫得惟妙惟肖,一時間20多家刊物競相轉載。
彭拜的家風很澎湃。很難想象一個只讀過小學、因失祜僅上了15天初中的人是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的,彭拜做到了,并且憑實力登上新中國安徽第一批專業作家的舞臺。彭拜決意“讓自己的一生,作為留給子孫的一本立身做人的教科書”,“言教固不可少,身教更為重要”。雖歷經坎坷,但家訓是“知辱者奮,懷志者韌”。晚歲四代同堂,其樂融融,然制作家規《子孫須記》:“再窮不訴窮,再苦不叫苦”,“此生不留恩仇怨,只向心田把愛栽”,“歡樂分到大家名下,痛苦埋在自己心里”,把家國之愛播撒人間。他和劉阿姨是恩愛的典型,齊家的表率。六個子女,艱難困苦玉成才,“陸紫侶”的一本書,裝幀設計編排印刷,合力為之,書名就叫《我們的爸爸》。他們把父母年輕時的肖像用電腦P上西裝婚紗,再和鉆石婚照“同框”,愛意盈盈。二老九秩,他們又奉上90朵玫瑰,灼灼其華。正是:“放眼回眸,看苦旅人生,過雨穿風,兩情堅兮同金石;新妝舊影,憶良宵花燭,移環解佩,閨趣盎然見性天。”
讀拜老的書不厭倦,好喜歡,感覺像春天。他寫活了家鄉,他永遠活在春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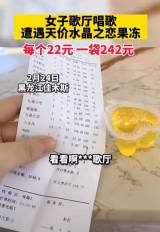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