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李聲波先生主編了一套文學作品集《江淮流韻》,其中有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把陽光裝在心里》。這書名盡管平實,但我覺得它似乎有著某種隱喻,當讀到《吾心閑處》《一米陽光》和《遠去的蛙聲》這幾篇文章時,書中所有文字都朝一種心性聚合,真意凸顯而明朗了。
結識聲波很早了,關系淡,未有過如切如磋。年輕時在《新安晚報》“人生百味”副刊上讀到他的文章,還是比較喜歡他在短小的篇幅中弄幾句題外話的閑情筆意。他其實一直保留了這種寫法,也仍然一兩千字的文章居多,沒有故意抻長,并且越寫越自然通透了。現在,我集中讀他的文章,發現他是“閑得真味”,有林下風致。
閑是文化,是境界,而非與忙碌對立;閑是般若,是性靈,也非與渙散同處。聲波能讓自己“閑”下來讀書,在余光中的詩文中丈量鄉愁,“先生的散文,延伸了鄉愁的長度。”在張愛玲的作品中觸摸她的傷痛,她的無盡的寂寞,以及煙花般絢爛的愛情。在豐子愷的散文中感受那種清幽玄妙的空靈,真摯樸誠的實在,接上他自己的氣韻流衍的閑心。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掂量生命,“淳樸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態”,認同“文學有文學的規律,文學就是寫人性的,脫離了人性,輕視文學規律,最后就是被文學拋棄。”
小說多是寫人性,散文也多是人性的投射。聲波幾十年來除了媒體人的新聞主業,還寫散文隨筆和文藝評論。寫得不太多。我想,與其說惜墨如金,不如說“閑心難得”,非到真正的閑靜之境不下筆,故而每有一作便是“閑得真意”。我這樣說的依據,是通過其文中情感而來的。他不回避自己接連幾年不陪母親過年的事實,“忽略了愛與被愛”;他感嘆:“其實回家的路并不遙遠啊……”聲波如此真情實感的文字,書中俯拾皆是,沒有至閑的心是寫不出來的,閑蘊純真,靜思人性。他對胡適的文學觀評價甚高,“他從中國詩文的衍變,認識了中國文學的癥結所在,他歡呼宋朝大詩人的絕大貢獻,認為其意義‘旨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于說話的詩體。’……他痛恨‘有文而無質’的歷史與現狀……”由此可見,聲波看重文章的內容及其真實性,而虛情和矯情的表達極容易在形式上暴露人性的不真或扭曲,他故而不為。還有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多情、濫情,也是貌似閑實則非閑,內心被某種東西控制的文字及文字支配的某種東西所累,他也不為。
“我總是期待著閱讀最真實的文字,期待著聆聽最真實的聲音,盡管很多時候都會失望,但依然不放棄對真實的渴慕。”聲波在《這個世界,我曾來過》一文中如此說,分明就是對自己交底了,閱讀的期待,也是寫作的期待,以真實抵達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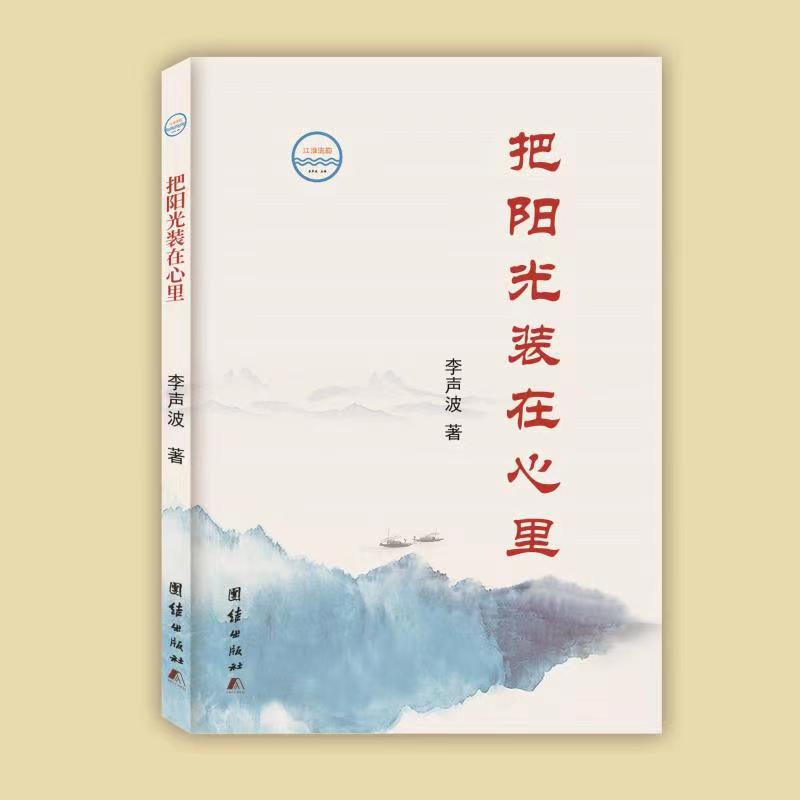
我從聲波游記類文章中,感受到他能夠做到“閑得真趣”——同樣是閑與真的指向。游記不好寫,要么是做景點介紹式的說明,要么是做風光拍照式的鏡頭直錄。或散漫而無主題,或聚焦而少空白。敘則一覽無遺,議則萬里無邊。有景有境而奇崛、有思有情而出人意表、夾敘夾議而邏輯自洽,太難太難了!我挑了幾篇聲波的游記來讀,感覺還是不錯的。這得力于他讀書多,人文素養見諸文字,他能將知識點融進景點,并轉化成個性語言呈現及形象化的鏡像,讀起來就有意趣了。秦淮、蘭亭、漓江、徽州、黃山、恒山等等人們非常熟悉的風景名勝,在他這里均成了“閑筆”,區別于數不勝數的游記,他構建的是思想者的通感,山河大地、人文淵藪盡萃于一生所秉持的理念,即“把陽光裝在心里”,每到一地,都是“一米陽光”的映照,外景即內境,寫景物就是寫他自己了。
聲波說:“我只喜歡這生活中的一米陽光,它就在案上。”案上的陽光,雖只有一米,但它可以移動到任何地方。故而,他游恒山,認識到恒山的“恒”,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故”,并且把兩者聯系起來,體悟到山的重疊險峻和博大雄渾之中人性的觀照,得其真義乃至真趣。
大自然的真與人性的真,是同構的,一體的。聲波可謂“閑識真面”。如何在“閑”中立住真文字呢?作為新聞工作者,聲波在進行散文創作時,從兩種語言系統出入往返恪守著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如山般真體內充,又如大自然般真與不奪。這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認知度與精神向度趨于匹配一致的維度,拋棄橫向線性思維,目光從山腳升到山頂,升到天空,貌似內容的虛化,實則視野的大化,意象真跡,真取不羈。“中國文化傳統的‘為尊者諱’的基因遍植讀者學人心中,于是如民族英雄般的偉大詩人形象,千余年來成為一座文學的巨峰,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其意義之深遠,已經不容人稍稍置上一喙了。中國人性格中的絕癥,是無中間路徑可走,劍拔弩張的結果是走向兩個極端,即神化和妖魔化。”(《撩開李白的面紗》)
聲波的書到手之后,我是最先讀《阮圩古井》,因為阮圩離我的老家小鎮只有數公里,很熟悉那古井,特別想知道他是怎么寫的,有沒有意味。他記憶中的“真實”的滄桑,已還給了遠去的往昔,時間填平了古井,而眼前的一無殘痕的“真實”又能保持多久?聲波對古井的回憶,由甘甜到苦澀,何嘗不是試圖撩開時光的面紗,看一看自然的本來面目,而即使“若干年后,人們挖出老井,看到石頭的痕跡”,也不可能找到曾經的印記,復原原來的影像了。讀完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有點沉重,做出了放棄回老家定居的念頭。想必聲波先生也有過回歸故園的心理糾纏,他的數十篇與往事有關的文章,背景就是故鄉的那方天空,那片鄉野。
我又讀到了一段真性情中見真面目的文字:“有時所見及所聞未必就是事情的本質和真相,總能從中領悟到許多深層次的道理。但偶爾,用簡單的眼光去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能還本自然。”(《花香秋意隨風起》)我不由得感喟:這樣好,不至于執念于真,也不依真起妄,為人為文通達許多。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