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quán)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wǎng)站或個人,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鏈接、轉(zhuǎn)貼或以其他方式復(fù)制發(fā)表;已授權(quán)的媒體、網(wǎng)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走進“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走進“天藍風(fēng)清語軟”的江南,便走進陣陣餛飩的撩人氤氳之中。
盡管江南很難劃出地理意義上的界線,然而從“欣見餛飩擔,且聞餛飩香”而得出“已作江南客”的推斷大抵是不會錯的。古屋高墻狹窄的小巷石板路上,餛飩擔與賣花女擦肩而過,那便是江南了;金字招牌俯瞰的老街中,金發(fā)碧眼們在導(dǎo)游小姐的示范下,用瓷質(zhì)調(diào)羹有滋有味地認識“餛飩”,那便是江南了。江南是枕河人家窗口垂吊到客船上的竹籃子里的兩碗餛飩,江南是午夜星月朗照下幽幽曲徑上游動著的餛飩擔上的小馬燈……
許是獨得江南文化的熏陶,那“一頭水鍋,一頭作坊”的江南餛飩擔,總讓人聯(lián)想到江南古民居客廳上那長長方方、玲瓏剔透、纖塵不染的紅木雕花茶幾,讓人睹物情生而“未食餛飩先醉藝”;那擔邊身著蘭花土布唐裝的餛飩師傅,那擔上隨風(fēng)搖曳的寫著“汪一挑”老字號的蘭花土布三角旗幡,又讓人陶醉于“幽雅老街品餛飩”的“青花瓷”氛圍。
驛路旅人則往往嘆服這古老國度的“流動快餐店”,一排小抽屜推拉之間竟能魔術(shù)般變幻出一疊光彩照人的餛飩皮、一碗芳香四溢的鮮肉餡、一碟香菜末、一壺醬油、一罐香油、一盤小蔥、一壇細鹽和一竹筒胡椒粉。即便是那只極為普通的紫銅鍋,居然也能出奇制勝地巧設(shè)隔板將鍋體一分為二,一邊為煮熟餛飩的沸水,一邊為入碗為湯的鮮湯。
爐膛里的火苗可旺可衰,控制火候的秘訣在于添加松明或一般木柴。因此,江南餛飩香,每每與山間松明香相溶;品嘗餛飩美食,便往往因平添幾縷詩意之火而成為美事一樁。
有人就發(fā)起思古之幽情,想:餛飩擔如此精巧絕倫,其發(fā)明專利到底屬誰?江南人會洋洋然讓時間倒退四百余年,讓那位江陰人氏徐霞客的英名再度沐浴一次欽慕驚訝的洗禮。徐老先生第一次游覽考察人跡罕至的黃山飽嘗饑餓之苦后,就從木匠師傅裝滿斧、鋸、鑿、錘等全部工具的擔子上獲得啟發(fā),而設(shè)制出一種集鍋碗瓢盆、柴米油鹽于一挑的“游山具”,于是隨時隨地均可自制飲食,保證了他重游黃山計劃的圓滿成功。
從“游山具”轉(zhuǎn)化到“餛飩擔”,是“霞客路”上開放出的另一朵奇葩,江南人就讓它永遠燦爛地鮮艷在民間文學(xué)史冊上了。倘若說,“游山具”造就了一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話,那么,今日餛飩擔深受風(fēng)景線上旅人們的青睞則是一種無比美妙的巧合了。
難怪人們都說“江南餛飩香”,我想,這“香”絕不僅只是說那紅透薄皮的鮮肉餡,和那幾點蔥花幾絲香菜末幾縷松明炊煙的吧?難怪享用江南餛飩者都喜歡輕捏瓷調(diào)羹,那沉淀于碗底深處的詩魂履痕,是無法用竹筷、鋼叉捕撈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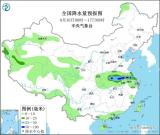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