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一些年里鄉村借事繁雜,日子不好過,借借還還如草榮草枯,一茬接一茬。
借事簡單,鍬锨鋤頭,轉個身子,到左鄰右舍就可借得,用完再轉身還了,一樁借事就完成了。招喚可打,可不打。升米、瓢面也是常借的,“淺升借米滿升還”,家家戶戶遵守。
鄉村的炊煙陸陸續續,或濃或淡或厚或薄,可沒見斷過。借得輕松平常,還得硬朗明白,鄉村多得是和美的氣韻。
鄉村的借事,還是有講究的,約定俗成,比如“借米不借柴,借衣不借鞋”,口口相傳,有道理,也有顧忌。米永遠可借,民以食為天,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皇帝還不打餓兵呢。家中斷頓,提著升子走上一趟,村陌多意,村人也不松泛,多走幾家,總不會空手回的。柴火就不一樣了,到處有的,樹枝、荒草、牛糞,都是燒鍋料。借柴火的人,肯定是個懶漢,借了,助懶漢的懶勁。“柴”和“財”還諧音,誰愿把財氣借出去呢?至于鞋子不借,也是有說法的,赤著腳多不礙事,何況草鞋都會編,湊合下就過去了。若借了,不小心穿破了,“破鞋”和破衣裳不同,破鞋有指向,說不上的別扭。“鞋子”還諧音“孩子”,虎毒不食子,再窮的家也不愿把“孩子”借與人。
鄉村的道理淺顯,顧忌中也約定了美好。
不過,借事從來就不是不可突破的。村子里的柱子,就什么都能借得。柱子是孤兒,七歲那年死了父母,算是吃百家飯的,守在父母丟下的三間草房里挨日腳。他什么不借呢?柴米油鹽,衣帽鞋襪,實際上柱子不需張口的,村子里東家西家南家北家,但凡能從牙縫摳出的都會送上門去的。柱子知好歹,遠遠地道聲謝,近近地說,借的,一定還。柱子在村子里活了下來,筋筋道道的,還算有點朝氣。
村子里最大的借事是借錢。
米、面、菜、油是自產的,錢就是另一回事了,有時一個村子里沒活頭錢,轉了一圈又轉回來,急得直跺腳。好在活人不會被尿憋死,終還是借到了。
鄉村為借錢找了個詞,叫“掇”錢,顯得鄭重,“掇”有文化,比“借”文氣。借錢時說得也婉轉,說,這幾天手頭急,掇兩個,十天半月就還。不提錢字,但也都知是錢的事。“掇”字有意思,“拾掇”常用。《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上有段子:“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沖撞;些小借掇,勉強應承。”此處的“借掇”曖昧,沒有鄉村的“掇”明快。
鄉村的借事正大光明,又被一句話固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掇了錢,說好了磅了肥豬還。放心,豬上了磅,錢還沒焐熱,人還沒到家,錢先還上了。借錢也沒有打條據一說,一句話撂下,板上釘釘子,人不死債不爛,何況還有父債子還頂著。
和借事沾邊的事,還有“行”,比如餓了“行口飯吃”,渴了“行口水喝”,路走黑到邊了“行個歇”,等等。行的事是不需還的,與借與掇有關聯,也有區別。不過總體上都是行個方便,與人方便也就是與己方便。“好事逼人來,天與行方便,紅裙情愿配袈裟,不待旁人勸。”村里人把行事做得順溜,模樣周周正正。
鄰村發生的借事更大。大剛子家出大事,幾間草房遭了火災燒個精光,八十歲老父親一口氣沒上來,去世了。大剛一夜急白頭,老父的喪事無處辦。村子里不止一家伸直了頸子,去他家辦。大剛感激涕零,在鄰家設靈堂,光光鮮鮮為父親辦了喪事。幾個老人抹著大胡子說話:“寧借屋停喪,不借屋成雙。”死者為大,也算救急。“屋成雙”是指給人做新房的,這房子不借。無理三扁擔,有理扁擔三。如此的借事,讓人感動。
柱子長大成人了,外出闖蕩,三十年后,柱子回村,一家家送上的紅包沉甸甸的,村子人集體拒絕,但仍像過節樣,戶戶請,家家接,柱子又吃了次百家飯。柱子含淚離村,不久為村子修了條路,路叫百家路,也算好借好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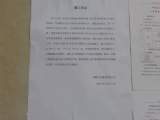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