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一次去江南,從合肥出發,乘火車到蕪湖,轉乘輪船,然后才踏上江南的土地。那個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青春躁動,躊躇滿志,不知天高地厚,受宣城同學之邀去他們老家轉轉。
同學的家鄉在宣城雙橋。輾轉抵達,覺得眼前一熱,似曾相識,仿佛夢中來過。時值仲春,漫山遍野的油菜花金燦燦的,綠水長繞,青山逶迤,村落小小。宣城的鄉下干凈,適合瞭望,宜于奔跑。他們拖著溫軟的當地方言,仔細真切地聽取,很快就能明白所有的人情世故。
所有的少年輕狂都是相似的。我們在學校熄燈后的宿舍里,高談闊論之余,淺薄地比較著各自的家鄉。同學來自安徽各地,大家爭先恐后、好狠斗勇般地比試。之于江南,我讀過許多關于小橋流水方面的文章,極想實地考察一番。于是,就有了這趟行程。那個時候,我尚不知道,這就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宣城的宣紙,彼時,在我眼里不過是一種特產。就像皖北盛產的香椿、芥菜絲一樣,集中在一個“吃”字。只是,宣紙名噪中外,屬于文化用品而已。
“少年心事當拿云。”走了一趟江南,我的心事里居然揮不去那些山山水水的影子。每次去文房四寶店里,隔著長長的柜臺,對著宣紙總有一陣出神的發呆。校園里還開設有書法課,三個學期換了三任老師。臨帖是顏真卿的各種碑。我寫的字,在畢業之即,老師說,距離配得上宣紙,還差幾年的功夫。我的眼前,浮現我們宣城之行看到的宣紙作坊,那些紙像我們中原的豆腐制作方式,有著同工異曲之妙。咦,宣紙如此之神奇。
2020年春節,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全民囚在家里,猶如困獸。我在家里找出唐詩宋詞,每天默寫背誦一首。此前,我讀書極少,如果說寫過的文字也有上百萬,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字匠而已。與此同時,宣城籍文化學者趙焰在這整塊的光陰里,常常夜半披衣起床,成千上萬的文字劃過指尖,像潺潺的溪流。他在默默地寫一本書,就是關于宣紙。
趙焰的每一個文字,都帶著江南的春風氣息。它們溫潤,潔凈,明亮,讓人讀起來覺得日子是那么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遇見過宣城之后,幾乎每年都要去趟江南轉轉,看那溪水,在沒有游人走過的時光里,不分晝夜地兀自流著,嘩嘩作響。讓人覺得江南只有一個季節,那就是只有春天。一個人,一輩子,只活在春天里,這該是怎樣的奢華?
趙焰寫江南,帶著自豪。此前,他寫淮河,寫江南,其實都是在寫歷史。在寫淮北時,趙焰對中原文化有過公允的評介。黃河流域,其實是粗獷的,領先的,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和中興地。至此,我懂得了少年的幼稚。所有的家鄉,之于每個人來說,都是最美的。對于生他養他的皖南,他不止一次地寫道:皖南其實是一個整體,集中體現著中國文化的諸多特征,集儒釋道俗于一身。趙焰自幼浸潤在書香里,邊讀書邊思索,乘車路過宣紙工廠,遠遠地他就暈車。在我看來,這是對皖南水土的一種投入,處于無夢無醒狀態。有暈眩,有夢幻,有腳踏實地的美食,充滿溫暖的人間煙火。
他走過道教的黃山齊云山,攀過佛家的九華山,邁過進取的宣州乃至整個皖南,閑閑地坐在書桌前,開始一部部地寫歷史,聚焦于皖南文化和晚清歷史。當然,還有一些關于宗教方面的思索,寫下來,或許并不適合于去發表,只是思想的結晶,像子彈那樣讓它先飛一會兒。
揮之不去的,可能還是家鄉的那些風物。一個人,最深的烙印,其實是在童年。那些書香,那些字紙,那些煙火,成就了思想,鑄造了習慣,穩妥了味蕾。或許,他并沒有意識到,寫宣紙,其實是為皖南立傳。如果是寫歷史,可以恣意縱橫,揮毫潑墨地寫意一般,不是有人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么。如果寫文化,站在成千上萬本書的巔峰之上,可以仰望,可以俯視,亦可以左顧右盼。唯有寫宣紙這樣的實物,需要檢索,需要躬身相向,有家國情懷,還有歷史淵源。這本最初命名為《宣紙傳》的書,歷經初稿,一改再改。在出版社催稿之際,趙焰又顛覆般地改了幾遍。直到宣紙被他改成了“一片云”。因為熟悉,所以無拘無束,大開大放,所向披靡,指哪打哪。深掘宣紙的前三朝后五帝,直指江南文化命脈。
作為法制報總編,他每天要看報紙大樣。我常常想,法治的終極目的不過就是讓人們過上心儀的日子,讓生活變得輕盈起來,可以體驗到午后陽光的溫暖,可以伏在案前,在宣紙上忽然有書寫或畫作的沖動。宣紙作為一種人文精神的載體,一直溫潤著,暖暖的,詩意地等待著。把宣紙寫到極致,既是論文,又是散文,還帶著歷史的氣息,宛若百煉鋼化作繞指柔的普世關懷。
在宣紙的千年等一回里,有個叫趙焰的皖南游子,在書山上為它做了一個唯美的標記,那就是《宣紙之美》。是為讀后感,不知是不是配寫在宣紙邊上。就像當年書法老師期待的那樣,尚需再練筆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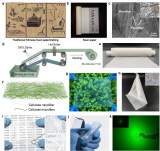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