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每年冬月,鄉下二姐總會打來電話:給你灌點香腸,腌幾刀咸肉吧。電話這端,毫無例外地欣然應允。
過不久,陽臺上,一掛掛香腸、一刀刀咸肉以及幾尾風魚之類,就掛滿了。看著這一切,想一位朋友說過那句“把日子過起來”,就暗自發笑。是啊,把日子過起來,比什么都重要。
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溫情脈脈。農歷最后一個月又稱臘月。有記載:“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歲末年前,囤年貨,腌臘肉。待地寒天凍,家人閑坐,燈火亦可親。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父親被落實政策后,我全家自鄉下搬回縣城。記得初冬時節,有位鄉親來訪。父親特意領他到廂房喝茶小坐。廂房的梁上懸掛著一大抱咸貨(無外乎咸肉咸鵝之類),特別顯眼。客人走后,父親對我們說:就是讓他看看,回到縣城,我們的日子過得還不錯的。那個年代單憑幾刀咸肉,幾只咸雞咸鴨,足以佐證在城里生活比鄉下不差,往后的日子也滋潤。現在想來,這其中自然有父親的虛榮心理,也可見那時日子的艱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弟妹尚在讀書,三個姐姐陸續出嫁,全家5張嘴吃飯,僅靠父親一人工資維持。每日柴米油鹽,蔬菜葷菜都要買。不比在鄉下,清晨,母親去菜園,不幾分鐘總能采回一大挎籃蔬菜。那臘月腌制的咸貨,也能吃到來年夏至。中午,炒幾碟鮮蔬,蒸幾塊噴香的咸肉,日子篤篤定定的,不慌不亂。
現如今,吃穿早不是問題,可每到年下總沿襲父輩的習慣,腌制一些臘味。自己也固執地認為這些臘味才是過年必不可少的元素。有了這一切,就有了對年的期盼,心里就踏實。
孩子們可不太喜歡吃這些咸貨。食品專業博士畢業的兒子和媳婦,曾多次建議我們少吃或不吃。他們哪里懂得,從小盼殺豬,殺鵝,等著這些咸貨過年的我們,記憶的味蕾里,早已存儲了噴香的臘味,每到年底,我們強大的胃,就會條件反射似的需要填充。一碗白米飯上,鋪一層青菜,搛兩塊咸肉,再挖半勺咸香的油覆至青菜上,感覺扒進口的每一粒米都滑溜溜的,充滿了幸福的香氣。
小時我隨全家下放去的那個小莊村,不過20來戶人家。春末,家家都捉來二三十只毛茸茸的小鵝仔回來。鵝兒漸大,早早晚晚的,伙伴們就趕鵝,去野外、去河里。鵝,在吃它的草,在河里嬉戲,我們在一邊瘋玩:挖老貓,瓦石子,跳房子,拔毛針……玩到天將黑,村口傳來呼喊“四丫頭、三犟仔……快回來吃飯啰”,才趕緊去鵝堆里,用長竹竿去分自家的鵝。那些鵝,都有各家的記號。或鵝頭或身體染上紅色,或鵝腳上有記號:什么雙腳里丫,左腳內丫,右腳外丫之類。每年我家的鵝,都是雙腳外丫,約定俗成的,別家也不重復。鵝很小時,將一只只鵝剪去外掌上的蹼,再用火燎一下傷口,此后鵝的雙腳就殘缺了兩塊蹼。如今看來,這做法挺殘忍。
臘月一到,那些肥墩墩的鵝們終歸逃不過一場宿命。將一只只大白鵝割頸,再用雙翅交叉將鵝頭反鎖綁緊。待一大鍋水滾開,倒入擺放在門外的大盆內,將一只只殺好的鵝按入水中,燙,乘熱拔毛。然后開膛破肚,洗凈,用大鹽粒腌。幾天后回鹵,風干,再幾個大太陽,那些咸鵝就曬得干薄薄的,咸香無比。村里一群牧鵝的孩子,此后無所事事。一日日地等待,眼盼著新年的到來。
臘月里,除了殺雞宰鵝。村里另一項重大活動就是殺豬、吃殺豬飯。誰家殺豬,幾乎一個村的人都會涌去。一大鐵鍋烀出的豬心豬肺豬頭肉湯(俗稱豬下水),一大臉盆油紅發亮的紅燒肉,幾大水桶盛好的白米飯。大人們坐桌邊喝酒猜拳,孩子們端一大海碗,吃著,跑著,鬧著。臘月黃天,陽光溫暖。家家門前掛著洗曬的各色被條,如彩旗般迎風飄舞。那是一年里最和諧,最美好的光景。
那天回霍山東西溪作家村,見一群人立于一農戶門前拍照。走近,見兩根長竹竿上掛滿了各種臘味咸貨。模樣雖不雅觀,卻令人浮想,切一盤蒸透后,它該是怎樣的有嚼勁又解饞,禁不住唾津潛溢了。
此刻,又想起那些年的臘味年味。
想起那些再不復現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溫暖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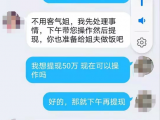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