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上周三那天,母親打電話來,說尼姑寺那塊菊花兩人摘不完,讓我周末沒事就回家幫忙摘菊花,省得她多跑幾次。
年過古稀的母親,總是不愿意閑著,自家地里都種上了菊花,還去租了人家一塊地。這幾年,每到摘花,她忙不過來時,電話就追過來。回家摘花,成了常態。我只要有時間,總得回去摘一天,山里人出身,是幫忙也是不能忘本。
一大早開車進山,車過桃源村,滿目都是黃菊白菊,成片成嶺的,氣勢恢弘地畫出鄉村大地上的美景。等我到家時,母親已經出門了,父親和妹妹在烘房里整理菊花,金絲皇菊黃燦燦的,倒進透明的塑料袋里,層層疊疊的,是一袋金黃的秋天,是滿滿的喜悅。
我推著扎了兩只竹籃的獨輪車出門,妻和妹妹跟在后面。出了村口,田畈里的黃菊,山巒間的貢菊,行走青山綠水間,心情大好。走了半小時,從大路到山徑,然后穿越茶棵地,繞過幾幢土墻舍,看到了母親俯身在一片貢菊花中。
“來了……”母親聽到我們的講話聲才抬起頭來,她的頭發跟菊花一樣白。貢菊綻放,站在路上看,似乎不是很大的一片,等置身花叢中,才發現菊花開得密密麻麻,看不見空地,不好下腳。掰開花叢露出空地,竹籃放進去,人站進去。人與菊花,融為一體。掰著花枝,每一朵綻放的花都要摘下。一朵,一朵……一把,一把……身邊的菊花地慢慢暗下去,竹籃里的菊花漸漸涌起。濃郁的菊花香,從指尖飄逸出來,帶著清新的山野氣息。
母親說種菊花要施肥拔草,掐頂疏花蕾。看似簡單的農事,對我來說已經很遙遠。我都是在秋天回山里,看到漫山遍野菊花開。菊花的移栽與照料,都是從母親口中得到的一些細節,只有靠想象去彌補菊花的成長。母親悉心伺候著菊花,從春天到夏天,然后是秋天,付出的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站在山巒上摘花,看著對面的人家,桃李蔭后檐,菊花繞羅堂。山里人家,只要肯吃苦的,那些艱辛的付出,回報總能得到慰藉。籃里的菊花滿了,母親說,倒到袋子里吃點面包再摘。天色卻不知何時變了,陽光不知何處去,陰沉的云霾壓過來,看著一大片菊花,心里頓有一層陰影。
雨的到來,菊花變得沉重起來,捏著都是水。母親和妹妹未雨綢繆,帶了雨衣,我和妻只有傘。妻說:“撐傘可以摘的。”母親不許:“你倆要不就回去吧,要不就折一捧到土墻舍屋檐下摘吧,地里風大。”大袋子里的菊花不能淋雨,我背到屋檐下,門是鎖的,家中無人。母親種的地,就是租他家的。
普通的土墻舍,屋檐挑出的不多。我再回地里抱回一大捧折下的菊花枝,母親也幫忙抱一大捧過來。我和妻就在屋檐下摘花,被蒙蒙冬雨打著。菊花枝葉濕漉漉的,枯黃的深綠的,粘在手上。還有呼嘯的寒風,凜冽著,這樣的時節摘花,有些無奈。屋檐下的風也大,旁邊的大樹都搖晃不止。一只小黑狗突然出現在面前,我抬頭一看,主人緊跟著到來。老人很熱情,開了廚房門說:“進來避避風,抱到里面來摘花。”花枝帶著黃葉黑葉,我不好意思抱進去。他拽了兩只大化肥袋來,鋪在地上,我抱了花枝堆在上面。
老人說,中午到他那里吃口熱飯。他在廚房里炒菜,我和妻摘花。我原以為幫母親可以早點回家吃中飯,可這雨一下,一切都改變了。老人的大兒子、兒媳,是我小學和初中同學,讀書時關系挺好。今年國慶,他們兩口子從上海回來,還約在小城工作的幾個初中同學一聚。
坐在家里摘花,多了幾分暖意。聽著房頂上呼嘯的風,看著披著雨衣站在地里摘花的母親,那種風吹雨打的味道,我不敢去想。老人飯燒好,讓我去喊地里的母親和妹妹來吃口熱飯。她倆說帶了面包和雞蛋,為了多摘幾朵花,就不來吃了。我和妻陪著老人一起吃飯、聊天,聊著尼姑寺。老人說,他父親當年遷來的時候,寺廟就剩墻腳那堆亂石,現在隔壁都做房子了。與寺廟有關的故事,我想知道,他說不上來。
簡單吃過午飯后,母親回來了兩次,籃里裝著、懷里抱著菊花枝,給我倆摘,她繼續回地里摘。雨卻絲毫沒有停的意思,風也是。過了一會兒,妹妹推著一袋菊花過來:“不摘了,太冷了,明天上午再來。”母親背著竹籃在她身后,頭發都濕透了。菊花雖重要,身體可是摘花的本錢。辭別了老人,在回家路上,邂逅了退休在家種菊花的小學老師,他在烘房里忙碌,我和妻在他那里聊了半小時,烘房暖意陣陣,真是不錯。
雨似乎是停了,風還是很大。穿著單薄的我倆,在回村的山路上,嬉笑小跑著取暖。到家時三點半,母親已經穿上厚實的棉襖,在廚房燒晚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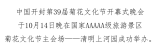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