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quán)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wǎng)站或個人,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鏈接、轉(zhuǎn)貼或以其他方式復(fù)制發(fā)表;已授權(quán)的媒體、網(wǎng)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wǎng)”,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zé)任。
孫仁歌散文集《淺水不養(yǎng)山》(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在為散文愛好者提供散文大餐的同時,談散文創(chuàng)作亦多有卓見。作者推崇“學(xué)者散文”,筆下散文自然也會撳下學(xué)者“思想”的烙印。于是,個中邏輯也就成了欣賞者的一把鑰匙。
“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養(yǎng)大了,翅膀硬了,就會遠(yuǎn)走高飛;可飛得再遠(yuǎn)再高,心里卻總是放不下這方水土,而且時間越是久長,這種思念就越是深切,以至夢繞魂牽,形成鄉(xiāng)愁。這種人之常情,注定了思鄉(xiāng)懷舊必然成為散文創(chuàng)作的熱門題材,注定了地域特色必然成為名家散文的鮮明印記。
孫先生筆下,故鄉(xiāng)那不起眼的小河,“在我童年時最清”;童年小鎮(zhèn)那“彎彎的、窄窄的”老街,卻有我“生命中的風(fēng)景”;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找不到家門的老宅“卻被我永遠(yuǎn)收到了心底”。《我夢見了父親的淚痕》一文,這樣描寫父親抽煙的情景:“小時候,我曾留意過從父親的口腔、鼻腔中冒出來的那裊裊煙霧,開始是直直的,不一會兒就變得彎彎的了,直到悠然淡去、散盡”,可謂直來直去,好聚好散,接著又重復(fù)。
覺得很好看,也很好玩,父親享受的沒準(zhǔn)也是這由里而外、猶如“神龍”破口而來,倏然之間又絕口而去的裊裊飛煙的風(fēng)景。“那絲絲縷縷的鄉(xiāng)愁,不也正如這裊裊飛煙”?只是孫先生的鄉(xiāng)愁,有里里外外多個層次:小河,小鎮(zhèn),老宅,屬于物質(zhì)層面,真;風(fēng)土人情,比如救英英時“好幾個叔叔輩的大人”的見義勇為,老趙的特別仗義和老姚的樂于助人,屬于精神層面,善;而最深的一層,則在文化層面,它觸及靈魂、銘心刻骨,美。“小時候,和哥哥們坐在一起聽父親吟詩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在哪兒聽父親吟詩?當(dāng)然是老宅。但老宅并無特別的景致,“院子里有兩株樹,一株是香椿樹,另一株也是香椿樹”。父親吟詩多在什么時候?“夏季納涼之際”。父親怎么吟詩?“說是吟詩,其實就是唱詩。”《聽父親吟詩》這樣描寫“吟詩成癮”的父親:“父親吟詩到動情處,也就不管你聽與不聽了,濃濃的詩意會把他帶到一個完全個人化的情感世界,眉睫之前似乎無物存在了,可謂如臻化境,大癡大醉都盡在其中矣。”值得注意的是,這兒父親動情的“情”,早已超出了一般感情的范疇,達(dá)到了人格、情操的境界:“是啊,在那個特殊年代,父親能清虛自守,以吟為常,既陶冶了兒女們的心志,又在不經(jīng)意間打發(fā)掉了許多孤寂難挨的日子,實在不同凡響,這也算是父親的一種生存方式吧”。特殊時期居然有此奇景,這樣的鄉(xiāng)愁,作為游子的根,能不溶化在血液中嗎?
志在四方的游子,往往隨遇而安甚至隨欲雅化,將對故鄉(xiāng)的感情遷移到自己學(xué)習(xí)、工作、生活的地方。孫先生筆下,《臨春的窗》《三月看桃》寫南大校園;《豆腐如詩》《洞山路上的風(fēng)景》《聽聽那鳥語》《田家庵的樹》寫淮南,無不一往情深,頗有“卻把淮南當(dāng)壽縣”的意味,只是尚未充分滲透職業(yè)習(xí)慣;但《淺水不養(yǎng)山》一文就不同了。
揣摩此文寫作緣起,是否當(dāng)時正在淮南師范學(xué)院為大一新生教寫作課的作者,因為“舜耕山下第一秋”這一命題作文,居然給筆者帶來了立意的尷尬“而操觚為之”?透過作者的選材立意、謀篇布局以至語言表達(dá),分明可以看出現(xiàn)身說法的意圖。先扣題,寫淮南境內(nèi)山有美名而水難媲美。再由八公山說到舜耕山,糅入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暗含自強(qiáng)不息之意,以身作則,埋下伏筆。作文之要,在厚積薄發(fā);教大學(xué)生作文,也是教大學(xué)生讀書。大學(xué)生作文,沒點(diǎn)書卷氣何足為訓(xùn),故作者旁征博引,反復(fù)渲染“治水養(yǎng)山”之意:“人不得養(yǎng),人躁;山不得養(yǎng),山枯”,筆落于山而意實在人;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但“水淺樂不起,樂山卻又不知山”;“山以水為血脈,山得水而活”,縱是名山,也會“因缺水而日見黯然無光”。
可嘆如此深遠(yuǎn)的命意,許多學(xué)生哪里明白,“來到舜耕山下這所高校,被他們視為讀書升學(xué)追求的一種失敗,理想王國的大廈轟然崩塌,深感前程渺茫,哪里還有余趣自引舜耕山下的那灣‘半畝淺水’去澆心中的塊壘呢?”要解決這種思想境界的問題,少不得高屋建瓴,從立德修身的高度耐心引導(dǎo),于是談舜之傳說,引孟子名言,最后告訴學(xué)生“舜耕山就代表一種高度”,“淮南得山而不得水,但擁有一山之呵護(hù)也就足夠幸運(yùn)的了”,“淺水不養(yǎng)山已成為事實,也難以改變,但人與山只要能和諧共處,默默滿足于一種寧靜致遠(yuǎn)、清虛自守的精神以自養(yǎng),山魂人魂也不至于速枯耳。”
說白了,就是要學(xué)生好好讀書,多多“蓄水”,以養(yǎng)自身之“山”。如此既教作文,又教做人,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真應(yīng)了那句話:三句話不離本行。
在地域特色與職業(yè)習(xí)慣雙輪驅(qū)動的同時,孫先生運(yùn)筆之靈性與智性亦相映生輝。時間這個話題該有多少人談過,又該產(chǎn)生過多少名作?《時間的魅力》一文卻另辟蹊徑,避開時間“逼人”的一面,挑出時間“誘人”的一面來說,別開生面,極富新意。“或許因為我們對于生命的長生不老乃至無限延長,有一種潛在的期待甚或奢望,所以我們有時才會擋不住時間的誘惑,以至于會不知不覺地被時間戲弄一番。”“被時間戲弄”?這問題頗似謎語,而謎底其實并不難理解:“時間有時的確很逗,也很虛偽,這就是時間差。”
以靈性獲鮮活與跳脫之效,以智性收深刻與豐盈之功,二者交相輝映,學(xué)者散文便多以思想見勝。孫先生類似篇章甚多,如《作為父親的余光中》,由“八根小辮子”搖曳出詩人父親“生活藝術(shù)化,藝術(shù)生活化”的慈父風(fēng)范;《學(xué)者型教育家黃德寬》,由“跪牛”形象引申出“做學(xué)問的黃德寬與做校長的黃德寬”這“一個人的兩個世界”,莫不鮮活生動而極富啟迪,都是靈性智性相映生輝,彰顯溫柔敦厚、雋永深沉文風(fēng)的好例。
那么,是否學(xué)者散文,只有溫柔敦厚沒有鋒芒畢露,只有雋永深沉沒有面紅耳赤?即以孫先生散文而論,還有另一道風(fēng)景同樣吸引眼球。學(xué)者散文,富于批判精神,敢于挺身而出,是勇敢;富于辯證思維,立于不敗之地,是智慧。倘若批判精神與辯證思維雙管齊下且相輔相成,對于“智勇雙全”的批評家而言,那就無疑是一種相當(dāng)高的境界了。
孫仁歌先生集學(xué)者、作家、評論家于一身,既能掄出散文的地域特色及職業(yè)習(xí)慣,也能掄出散文的靈性與智性,更能掄出評論家的批判精神與辯證思維。說到底,還是更看重散文見真境界這板斧,激濁揚(yáng)清,虎虎生風(fēng),更來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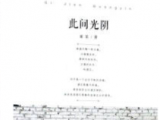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