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張詩群的散文在結構上基本上都像小說一樣精巧,幾乎每一篇都是一個故事,也幾乎都是用濃厚的散文語言在說一段往事,故鄉的往事,童年的往事,真的,往事并不總是如煙。遙遠的往事就像陳酒或濃茶,醇而厚,苦而甘,銘心有由,回味無窮。能夠娓娓道來的往事定是最不能忘懷的,無論是美好的,還是凄涼的,哪怕是美好中帶有一點缺憾,凄涼中夾著一絲喜悅。
聞一多說,家鄉是個賊,他能偷去你的心。讀罷掩卷,想來這個“賊”無時無刻不在啃嚙著張詩群的心,勾起她懷舊思鄉的念頭,野童村姑、慈母嚴父、憨叔悍嬸全涌進了你的腦海,揮之不去,不招即來。往事的魅力不僅于作者欣欣于筆,于讀者也是躍然紙上,喜悅中的苦澀,歡樂中的惆悵,回味童年的青澀和天真,眷顧家鄉的風俗與人情。
《遠去的渡口》用強烈對比的情境,敘述了枝子的自由和童年的圈囿。枝子逃學,和男孩子摔泥巴,只身無伴去黃墓渡,而相比之下,“童年”置身于小腳奶奶的“安全網”里,最多只能吐吐“幽涼的信子”。終于在枝子的“誘惑”下,結伴去了十里之遙的黃墓渡。因為“一聲招呼也不打”就去了,換來一頓毒打,卻并沒有湮沒童年“去黃墓渡的快樂”,甚至在夢中都懷念那“淺黃色的河水”“濡濕熱鬧的街道”“粘著晶片的蝴蝶結”和“河水的柔滑和荒涼的溫暖”。小說式的散文,在情節和語言上也有起伏跌宕,這可能是詩群寫作的一慣的風格,譬如,《土》《依稀采蓮》就是。
詩群的散文能把你帶進一個農村風俗畫的畫廊,無論是丹青,還是素描,都值得流連駐足,仔細品味。美好的情緒中帶有一點點惆悵,卻又不會將惆悵放大,而破壞了基本格調和風格,那格調是愉悅而不哀怨,那風格是積極而不消沉。即便是《土》中銀花、改子的躁動童年、出走少年,似乎是歧路操業,作者不動情的敘述都是那樣沉穩,沒有世俗的那樣“怒其不爭”的感情偏倚,而青衣“一定很美很美”是作者對水杏歸途的贊賞和認同。《土》中三個女孩命運折射出時代的多彩和多元,離土的無奈和無助,“打工”的銀花、“坐臺”的改子和“青衣”的水杏,雖是中國農村部分青年的縮影,寫來卻是栩栩如生而又張收恰當。其中的“學來的《西廂記》”和“磕破了膝蓋”兩段文字相當的生動,水杏的“天才”和“堅定”,傳遞著作者對水杏的偏愛和深摯。
《明月曾照彩云歸》就是淡淡的水墨丹青,那流淌在秋夜的月光,那彌散在院落的桂香,那發酵的心情,那慈祥的蒼老,無一不是曾經的鄉俗,遠去的時光,就連那月餅的分食也是那樣溫馨,不緊不慢,說盡了回憶的魅力,道盡了親情的溫暖。
《有些路是溫暖的河流》和《醒著的暗夜》,可以看作農村年、節的風俗畫,素寫白描,情緒的張放盡在平靜的敘述之中,基調的歡快也漲溢在字里行間,對童年的記憶清晰得可以娓娓于“細微末節”,對往日的留戀幾欲可重回過去。
《依稀采蓮》是一篇典型的詩群式散文、散文式的小說。香秀的活躍和彩龍船的紅火,是分兩條線展開的,既齊頭并進,又此起彼伏,沒有“尖銳鑼鼓”和“軟語小調”,就不能突出香秀的才華,而沒有香秀“鬼攆了魂”似的“跳跳跳”,就掀不起“紅色旋風”的高潮,相輔相成,互相烘托。在狂歡的艄公、丑婆之中,香秀是那樣的“碎步搖搖”,那樣的“粉面桃花”,那樣的“裊裊婷婷”,簡直就是一個“凌波仙子”。在一切平靜之后,依舊鋤地,依舊采菱,依舊春種秋收,依舊麥黃稻熟,似乎沒有“一絲懷念那個沸騰的元宵節”。其實不然,香秀對演出的執著,對彩龍船的迷戀,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一次又一次拒絕前村后莊熱情的說媒提親”,便是對生活寄于奢望的證明。多年以后,胖而健壯的采蓮女“神情安定地賣一籃豆芽”,可能采蓮女早就淡忘了當年的熱烈和美好,可作者依然記得香秀當年的風采“曾經那么純美”,美好的往事帶著缺憾,苦澀的生活承載著艱辛,此刻,生活的意義,作者也許比香秀體會得更加深刻。
詩群的老家在繁昌,我在繁昌生活了十五年。每年春末,“賣茶葉”的聲音滿街遍巷,一聽到“賣茶野(葉)”,我們家老鄭會說,你的老鄉來了。人生有幾個十五年?自然,繁昌也就成了故鄉了,至少是半個,如果有“半個故鄉”這種說法的話。
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有獎征集新聞線索,可以是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一經采用將給予獎勵。
報料方式:新安晚報官方微信(id:xawbxawb),大皖新聞“報料”欄目,視頻報料郵箱(baoliao@ahwang.cn),24小時新聞熱線:0551-62396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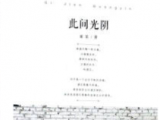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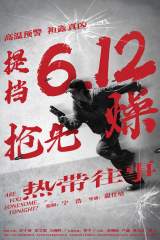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