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最近有點魔怔,看《人世間》里面人進屋就干活,心想不是應該先洗手嗎?換到《心居》,看里面各種吵吵,就想勸一句,自己人別折磨自己了,省點精力對付無妄之災不好嗎?
疫情兩年多,不覺生出新的本能,看任何事物都會加上疫情濾鏡。比如重讀盧照鄰的《長安古意》,“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心想,這要是寫進流調報告,分分鐘被社死啊。
更不用說“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云”,妥妥的聚集加無防護,又是長安這樣的大城,有點啥事就是大事。
但也因此更加感到某種偉大,江河萬里,泥沙俱下,少了點整肅,但容許人人都有點英雄梟雄氣質。就像一個特別健康的人,不怕吹點兒風淋點兒雨吃點不干不凈的東西,你看《水滸傳》里有哪個英雄點二斤熟牛肉時會問保質期,就一個宋江,是個吃幾口鮮魚就要鬧肚子的主。
《長安古意》據說原本發端于宮體詩,宮體詩指以南朝梁簡文帝蕭綱為太子時的東宮,以及陳后主、隋煬帝、唐太宗等幾個宮廷為中心的詩歌。其內容多是宮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則追求詞藻靡麗。
的確,這首詩里有宮廷,也有男女,但是辭藻不能算是靡麗,而是華麗得生機勃勃: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百尺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游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
“長安大道”四字,奠定了整首詩的氣象,即便接下來是“連狹斜”也沒關系,我們知道這是一座大城,像王小波最為推崇的查良錚的譯作: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相形之下,柳永寫杭州的那首詞,說了“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說了“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像個滿頭珠翠的美艷貴婦,夠美,但不夠強。傳說金人讀這首詞而起了覬覦之心,怕是無稽之談,但是這首詞里展示的杭州,就是很容易被壞人盯上啊。
而這些大道連狹斜,個人私域容許被保留,甚至水漲船高,也要飛揚一把,不辜負這偉大的時代。

怎么做才不辜負?有人寫詩,有人做官,有人要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都是想把自己盡量抻開。所以開豪車(青牛白馬七香車)有什么不對?把房子弄得奢靡華麗(雙闕連甍垂鳳翼)有什么不對?在街上看到喜歡的人,不用刨根問底,就在心里放一把火有什么不對呢?
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云外直。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
不相識才好,只愛陌生人,去他的知根知底,和陌生人的戀愛才是更讓人激動的冒險。這種戀愛當然也不會管柴米油鹽,只想問你如何追歡逐樂:
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
辛棄疾的警告就在耳邊:“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她們也有現成的話等著:“得成比目何辭死,愿作鴛鴦不羨仙”,好像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但心情已經被悉數傳達,管他塵土不塵土,我只要這一刻的盡興。
因為不盡興太討厭了:“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生憎帳額繡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一個“憎”字態度鮮明,人生苦短,就要和清心寡欲勢不兩立。
不要跟詩中人說“相愛沒有那么容易,每個人有他的脾氣”;不要說“轟轟烈烈不如平靜”,糟心的戀愛不如“一杯紅酒配電影,舒服窩在沙發里”,詩中人元氣沛然,越戰越勇,與有情人做快樂事才是最好: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郁金香。
片片行云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
當然,男人還要更自由一點, 他們以各種身份穿行在長安城,用主體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看到“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看到“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幰沒金堤”,這是一個有序的世界,也是一個明面上的世界,在這樣的秩序井然之后,還有暗流涌動。
“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
“探丸借客” 的典故出自《漢書·尹賞傳》:說長安閭里少年——差不多就是漢朝古惑仔,蔑視法律,受賄報仇,制作紅黑白三色彈丸,摸到赤丸者殺武吏,摸到黑丸者殺文吏,摸到白丸者給同伙治喪。
后來這些為非作歹的家伙都被尹賞收拾了,有的被處刑,有的被招安,可是盡管我們熱愛“武官馬上安天下,文官執筆定乾坤”的太平時日,還是想對古惑仔的世界探一探頭。
文藝的世界不只有真善美,還有惡之花,村上春樹說:“當我們打算寫小說,打算用文字去展現一個故事時,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東西便不容分說地滲出來,浮現于表面。作家或多或少都要與這毒素正面交鋒,分明知道危險,卻仍得手法巧妙地處理。”他說,這或許同河豚身上有毒的部位最鮮美甚是相似。

如果我們可以窺視唐時的長安,想看的,一定不只是歌舞升平萬邦來朝,還有那些“毒素”:黑暗處的交易,人性原始的蠢蠢欲動。文學作品不是社論,“正確”不是核心價值。馬伯庸的小說《長安十二時辰》就像是從這幾句詩里化來,黑衣人飛檐走壁,在我們入睡之后,世界是他們的: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云。
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
百姓們只管醉生夢死,一點小小欲念的飛升就會很快樂,肉食者則將長安當成比拼權勢的舞臺,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
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風。
這些炙手可熱的人,以為人生可以永遠處于高光時刻,要將自己的小宇宙不斷擴張。就像《紅樓夢》里的王熙鳳,總覺得富貴已經被她養家了,還可以養得再肥碩一點,就算秦可卿臨死之前對她發出預警,她還是只管問,有什么辦法可以長葆富貴?
她不知道,轟轟烈烈瞬間就能坍塌,這看似收拾不盡的繁華,忽然就能“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當時只道是尋常,以為不相讓是尋常,逞意氣是尋常,眼前這亂糟糟各種喧響是尋常。可能在這樣的熱鬧中,也會有小小的踩踏,對有錢人羨慕嫉妒恨,煩歌姬太妖嬈引發糾紛,你不知道,這財富妖嬈紛亂都是盛世的底氣,只有在盛世里,才能這么理直氣壯地拒絕節制。
當然,再這么寫下去三觀就太不正確了,而且,樂極真的會生悲,于是作者筆調一轉,寫道: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一個熱氣騰騰的世界,忽然就戛然而止。人們路過那時代,像《聊齋》里的書生把一場夢幻看做實景,黃粱一夢,滄海桑田,白玉堂變成墓碑前的青松,改變原來是這么容易發生的事,讓人不知道說什么好。
唯有寂寞永恒: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這個結尾是有點沒意思,很掃興,像是在說,戲里的人總要化為塵土,冷眼旁觀才是智者。但是真用不著有這種優越感,這樣的表達,在歷代詩詞里實在太多,人們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恐懼的,因為恐懼而節制。唯有這首詩,讓欲念縱橫,若你在最好的年華里,讀了,會為之血脈賁張,在不那么好的時光里,想起來,是惆悵加怦然的五味雜陳,它不是時代的眼淚,是盛世的絕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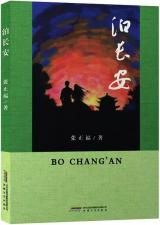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