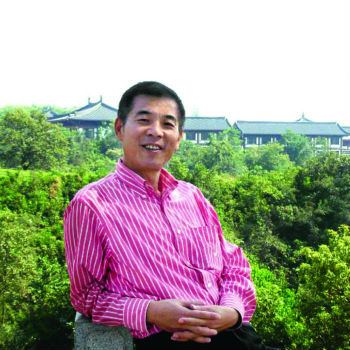
我與《新安晚報》的淵源很深,從創辦至今,25年來記不清寫過多少文章。
《新安晚報》創刊那年,我在銅陵市郊區文化館工作。因為熱愛文學,多次給《新安晚報》副刊投稿,引起了馬麗春老師的關注。在近小半年投稿之后的1993年5月28日,馬老師發表了我的散文《家住銅陵》。第一次看到刊有自己名字的文章出現在“人生百味”副刊上,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這樣一個工作在最基層的無名之輩,能有機會在省級晚報上發表作品,那是我做夢也不敢想的啊。打那以后,我開始訂閱《新安晚報》,就是為了閱讀副刊過癮。同時給副刊寫稿,我樂此不疲。
1998年7月的一天,頂著炎炎烈日,我和馬麗春老師第一次在報社副刊部見了面。我既緊張,又忐忑,大汗淋漓。馬老師笑著說:“哦,你就是王唯唯啊,我和我們總編都覺著你是個女的。”她的一句玩笑,一下子消除了我的緊張不安。接下來的聊天中,馬老師告誡我:“要多讀書,多體驗生活,不要急著寫。要多看多想,然后慢慢寫。”這樣的鼓勵和指點,讓我心里暖暖的。由于馬老師還有一個會議,她介紹我認識了黃從慎老師。由于不熟悉,都是黃老師問一句,我答一句。見我一頭汗,黃老師特地跑到樓下給我買了一根冰棍。在送我下樓時,黃老師說,今后有好作品就寄來,不管是寄給馬老師還是我都行。
2001年9月,我從銅陵調回合肥時,《新安晚報》已遷到安慶路。我又一次拜訪了馬麗春老師,可惜那次沒見到黃從慎老師。也就是那一次,我帶去了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人生散墨》。我恭恭敬敬地交到馬老師手上,說這本散文集里的大多數散文都已經在《新安晚報》上發表過。
《新安晚報》影響我到什么程度呢?我舉兩個例子。其一,去年我去廬陽區給一個單位排節目,在區文化館的同志介紹我后,那位負責人看看我說:“您是在《新安晚報》上常寫文章的王唯唯嗎?”我說:“是啊。”他高興地說:“我老看您的文章,今后有需要我幫忙的說一聲。”其二,我所居住的劇團大院門前有一賣鹵菜的大姐,一天去她攤位買鹵菜,見她正低頭看報,走近一瞧,是《新安晚報》,而且巧得不能再巧的是,那天晚報發表了我的《朗讀者》。從此,我和那位大姐相識了。此后,只要我在晚報上發表了文章,只要她看見我,她都會說報上又發你文章啦。
很多年來,已經有了這樣的習慣,每每寫出新作時,總是會自問:能不能先發給《新安晚報》看看?在我看來,一個好的副刊,是讀者、作者和這個報紙最有感情、也最能產生感情的地方。不僅如此,一個好的副刊,也是最能體現一家報社文藝水平的地方。
新聞報道要求真實、客觀、及時,有時甚至要爭分奪秒來報道;而副刊的內容豐富多彩、五花八門,有時效性要求也可以不受時間限制,既可以有要求真實的人生百態,也可以有情理兼到的文史小品與語言銳利的雜文短稿。自然這樣的副刊,對報紙而言,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所以好的副刊,是最能體現一家報社的辦報水平的。也正因為如此,數量、質量一直保持幾十年不變的副刊,為數不多,《新安晚報》的副刊便是其中之一。這就是一個好的副刊的魅力,也是其他版面沒有的一種文化現象。
“為老百姓辦,給老百姓看。”25年辦報宗旨堅持不容易,25年發展更讓人充滿敬意。現在我已經退休了,閱讀《新安晚報》就成了我的精神早餐。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樓從報箱里取出報紙,泡杯茶,點根煙,一個版面一個版面地看。當然,作為重點必看的內容,就是副刊“城事”。我是一個有四十多年“文齡”的老文青,在我看來,閱讀文學作品,幾乎可與衣食住行并列。
行文至此,回憶起和《新安晚報》編輯老師交往的點點滴滴,心里滿懷著由衷的感恩,這種感恩,是一條綿延不斷的溫暖清流。作為晚報的忠實讀者和寫作者,借晚報創辦25周年之際,說一聲謝謝!
(作者王唯唯 安徽省文化館原館長)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