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明代,合肥籍的科舉進士共有七十余人,其中萬歷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進士竇子偁,是較為特殊的一位。時人贊譽其“才具敏毅,持以凝重”,為官晉江,被任職地區的百姓建祠祭祀。仕宦生涯中深度參與了萬歷朝兩次影響力較大的政治事件,“性鯁直,敦厲名節”是對他一生最可貴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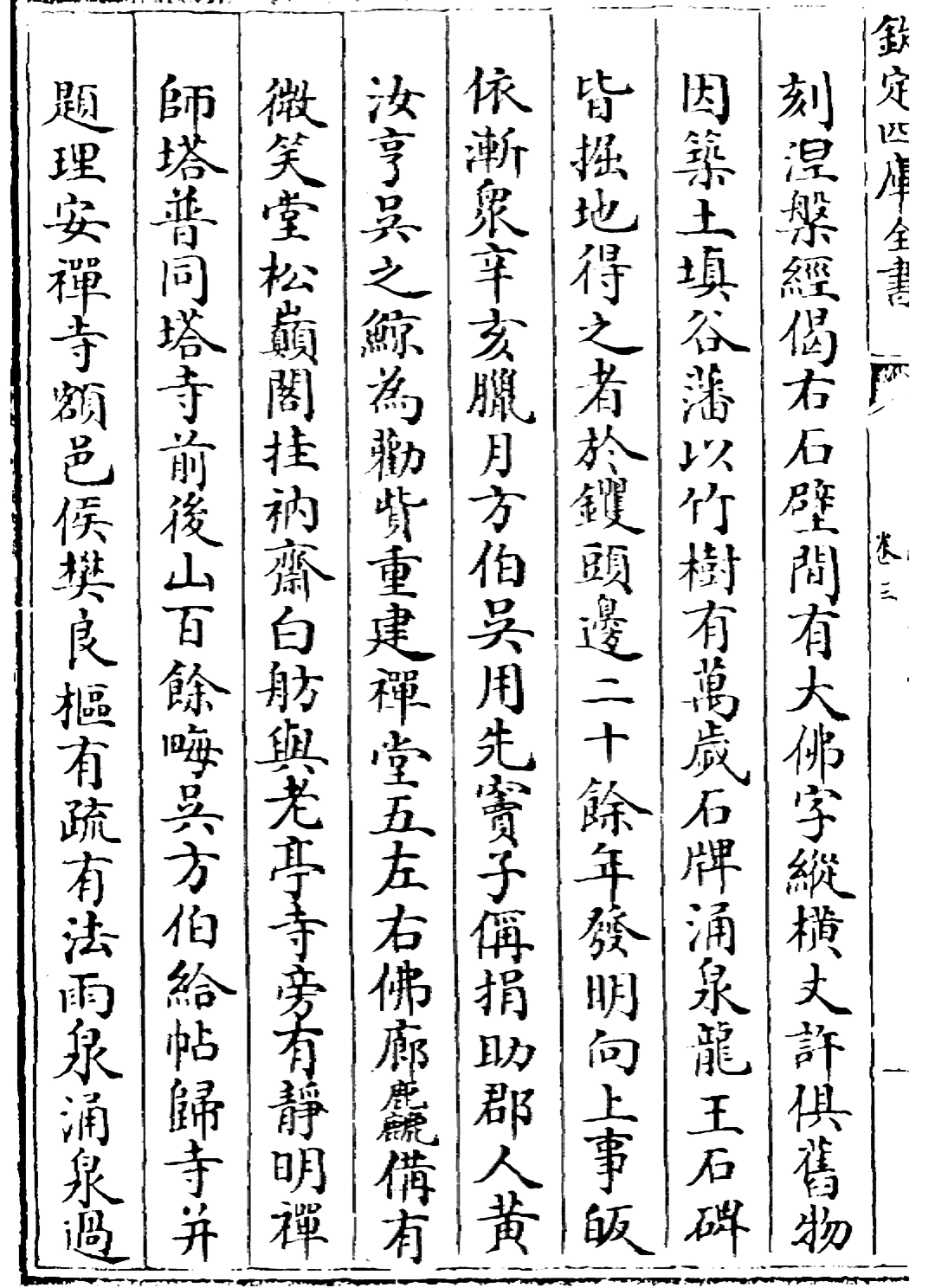 明吳之鯨《武林梵志》所載竇子偁重修涌泉禪寺事跡。
明吳之鯨《武林梵志》所載竇子偁重修涌泉禪寺事跡。
泉州郡守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記載:“竇子偁,直隸合肥縣民籍,萬歷二十年第三甲第一百二十一名。”
按《竇氏族譜》記載,其先祖竇伯言始遷居合肥,至第五代竇永隆時已擔任鄉飲大賓(明朝鄉飲儀式中的重要角色,需經府州縣三級舉薦,并將其姓氏、籍貫、事跡上報朝廷審核通過后方可獲任),可見其家族在地方已經頗具影響力。
萬歷十三年(1585年),竇子偁鄉試中舉,但其后又蹉跎了好幾年才考中進士,授官正七品大理寺評事,正式踏入仕途,這一年竇子偁32歲,剛過而立之年。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四月,竇子偁出任貴州鄉試官,后升戶部郎中,前往宣府督餉。這一職務是肥差,但竇子偁在任上“精心任事,不私一錢”,每年羨余高達六萬兩白銀,竇子偁一文不收,盡入府庫以為官用,朝廷特地予以嘉獎,足見他清廉淳厚。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前后,竇子偁外放擔任泉州知府。泉州與合肥人歷來頗有淵源,包拯之父包令儀曾知惠安縣,明人蔡悉也曾通判泉州府。竇子偁在任上,敢于任事,雷厲風行。道光《晉江縣志》有“咸相誡,不敢犯”的評價。
明朝晚期,地方豪強兼并土地十分普遍,甚至敢侵吞學宮,且“據法持衡”。面對錯綜復雜的地方關系,竇子偁并未選擇妥協,他下令將豪強侵吞的同安奇江莊525畝官田收回,并將歲征銀用以備修治齋舍、祭器及賑濟貧困學子。
泉州衛士卒的糧餉由泉州府供給,但胥吏大肆侵牟,以致士兵困苦,多有怨言。竇子偁下令“如期給之,寸鏹粒米無扣減”,泉州衛士卒的月糧終于得到了保證。
安平縣自宋時而建的石井書院被豪富侵奪,其家奴甚至凌侮前去理論的學子。最后在秀才黃汝良等人的抗爭下,竇子偁親自出面勒令歸還書院,并要求該豪富出資修繕。之后,竇子偁還捐出俸祿修繕書院。
為官多年,竇子偁自己的生活卻十分清貧,“從二三廬兒,取足給烹爨而已。俸錢外,矢不入官。入覲戒發,行李蕭然”,可見其高風亮節。
對于竇子偁“修學宮,清射圃,折節衿髦”的賢行,泉州百姓感念懷遠,《古今圖書集成》稱“清操大著,吏民畏而愛之”。道光《晉江縣志》稱“郡士民相率建祠生祀之,勒碑紀焉”;泉州籍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特地為其作《郡守合肥竇公去思碑記》《泉州衛散餉記》;閩人何喬遠贊譽“太守謂誰?淮南竇公也”。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戊辰,竇子偁因吏部考核優秀,升為湖廣布政使司提學副使。
楚藩之變
竇子偁在長沙時“置學田,修王惠橋”,同時也積極發掘諸如李若愚等地方人才。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長沙府善化縣縣學“殿堂盡頹”,竇子偁與南安知府黃洽中率領諸庠生重新修繕。但令竇子偁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件大事差點讓其命喪其中。
同年九月,楚王朱華奎為取悅皇帝,決定敬獻兩萬兩白銀“以助殿工”。這批庫銀剛剛到漢陽府,便被以朱蘊鈐為首的楚藩宗室攔劫,時稱“劫杠案”(民間呼進貢的物品為“皇杠”)。漢陽府立即拘捕了帶頭行劫的宗犯32名(一說36名)。但出人意料的是,為首的朱蘊鈐和朱蘊訇居然掙脫枷鎖,當場將巡撫趙可懷活活打死。此時湖廣巡撫衙門外聚集了數千名手持兇器的楚藩宗室,胥吏兵丁嚇得一哄而散。在撫院衙門的竇子偁被打成重傷,另一名副使周應治則更加倒霉,被扒光衣服一通亂打。宗人劫出32名案犯,將撫院收繳的皇杠重新搶走后,又包圍布政使司衙門索要庫銀,漢陽府為之大亂。
此時除右參政薛三才與按察使李燾在各自衙門堅守外,其余官員及家屬皆四散逃避。正在荊州巡視的湖廣巡按御史吳楷,得知消息后緊急奏報朝廷,并率人趕回府城控制事態。竇子偁等人被藏匿民間而得到救治,周應治由于傷勢過重又斯文掃地,事后致仕歸鄉。首輔沈一貫將這一惡劣事件定性為起兵叛逆,等同于正德年間的“宸濠之亂”,決定動用軍隊“平叛”,命鄂境嚴兵戒備。附近地區因而哄傳楚宗室“稱兵謀逆”,人心驚惶不安。鄖陽巡撫胡心得等人甚至集結兵馬,請求會師進剿。于是,一件宗室刑事犯罪案件被人為擴大成“謀逆”。
盡管竇子偁差點被瘋狂的楚藩宗室活活打死,但是其為防止事態擴大牽連無辜,于是上疏“憫楚宗人冤,馳疏請雪”,希望不要牽連無辜,不要擴大事態。湖廣按察使李燾也堅持上奏懇罷五路官軍,積極勸說宗藩,只派出胥吏就控制了局面,出兵之舉至此取消。竇子偁的舉動觸怒了想通過劫杠案打擊楚黨的浙黨領袖、內閣首輔沈一貫,“忤權相弗避”的竇子偁最后升為福建布政使司參政,被調離湖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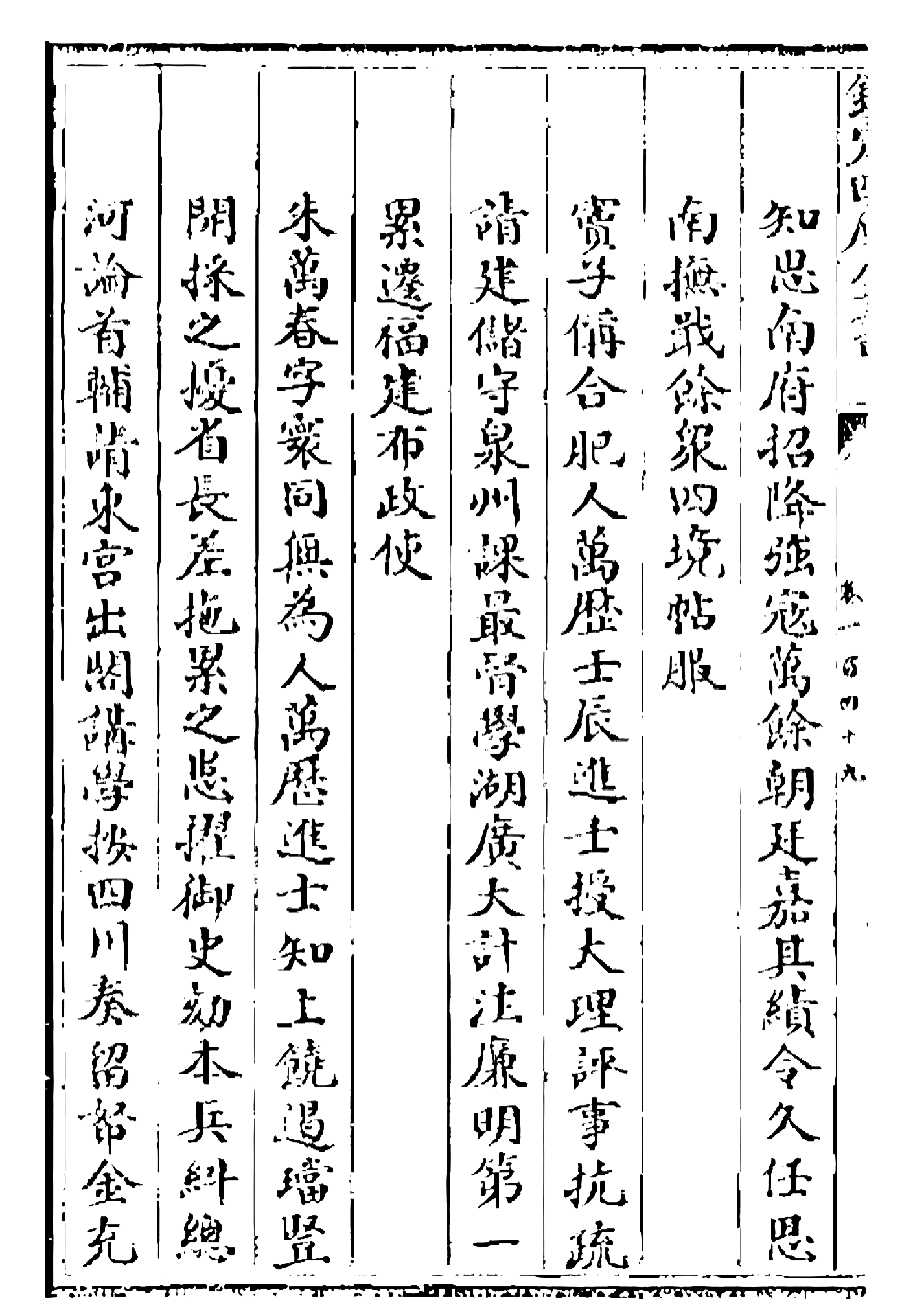 《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竇子偁本傳。
《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竇子偁本傳。
浙閩之終
竇子偁之后的仕途,一直在各省間來回奔波。先從福建右參政除為江西右參政,屁股沒坐熱又改山東右參政。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改浙江按察使,之后升為布政使。竇子偁在浙江任上,“剛毅敏決,雖婦孺知其名”。
竇子偁在參觀西湖時捐資修繕了與虎跑相提并論的涌泉禪寺(今理安寺),重新修繕海寧縣的義民倉,并為余杭縣儒學發銀四十二兩,贖買田七畝,坐落于下湖壩為縣學使用。在此期間,其著作《敬由篇》也在浙江付梓面世。
但堅守道德與廉節的竇子偁很快在浙江也待不下去了,原因是有人按照慣例將賦稅“羨余”送給他,竇子偁勃然大怒,斥責道:“朝廷方憂乏餉,安得羨余!若輩敢污吾地耶?速去!毋以身試法!”命令仆人打水,親自洗地數次后才止。竇子偁不肯同流合污的做法影響到了不少官員的利益,于是為人所構陷,只好稱病準備致仕,但由于清廉“歸裝不能辦”,數月后起復,任福建右布政使。
當時福建海防乏銀,竇子偁設法籌措,“預放六月軍糧,潛弭荒變”,成功為當時御敵海寇的福建解決了一時之需。但流年不利,福建市舶司內官高寀胡作非為,虐民甚慘,甚至里通外敵。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其在福建激起民變,數千百姓直接包圍了衙門。
袁一驥曾先后五次上書彈劾高寀,所以他懷疑民變就是袁一驥在背后主謀,于是帶著兩百多士兵劫持了袁一驥。聞變之后,竇子偁立即趕往巡撫行轅,也許是擔心高寀做出過激舉動,他在節鎮坊徘徊不前,沒有及時參與營救工作,后為袁一驥所記恨。
很快,竇子偁因京察被斥,決定辭官歸鄉,數年后郁郁而終。竇子偁去職,時人感慨其“清介絕俗,所至有聲,為江北人士之冠”。
竇子偁是合肥竇氏家族十三代中官職最高者,一生為官清廉耿介,不肯阿附流俗,其道德、品行、操守堪稱風氣日下的晚明官場的一股清流。 (楊義安 陳恒)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