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皖新聞?dòng)浾呤鹈淖帧D片,版權(quán)均屬新安晚報(bào)社所有。任何媒體、網(wǎng)站或個(gè)人,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鏈接、轉(zhuǎn)貼或以其他方式復(fù)制發(fā)表;已授權(quán)的媒體、網(wǎng)站,在使用時(shí)必須注明 “來源:大皖新聞”,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zé)任。
手機(jī)不離身,是現(xiàn)代人生活的常態(tài)。即使離一小會(huì)兒,那也不行,就像丟了魂似的。
手機(jī)改變了人們表達(dá)方式。從前慢的日子表達(dá)“今朝清晴可嘉”,如民國(guó)文人沈啟無,他遇到好天氣,心情愉悅,就趕緊寫信告訴朋友,分享他的快樂,天真又風(fēng)雅。現(xiàn)在人表達(dá)“今朝清晴可嘉”則用手機(jī),美景先與手機(jī)欣賞,美食要讓手機(jī)先“吃”,然后,迫不及待地說與發(fā)布。于是,就有了朋友圈,在那個(gè)“圈”里,無數(shù)新鮮事被更新鮮的事覆蓋,湮沒。無論是讀書還是做事,始終惦記著朋友圈的更新、點(diǎn)贊,在網(wǎng)上的滾滾煙塵里,找到一種滿足感。
自從有了抖音、快手等軟件,早上起來刷,晚上睡覺前刷,白天零碎時(shí)間也在刷,時(shí)間就在“刷刷刷”聲中不知不覺流逝了。無論是聚會(huì)、游玩,完事后,大家低頭各玩手機(jī),成了一道景觀。
大人帶小孩訣竅,就是給個(gè)手機(jī),孩子安靜,大人心安。鄰居小孩才二歲半,路都走不穩(wěn),話也說不清,但手機(jī)玩得很溜。有次,在電梯碰見,那小孩捧著手機(jī),手指靈活地觸屏滑動(dòng),前進(jìn)、后退、返回,非常專注。孩子奶奶說:“我們也擔(dān)心會(huì)把眼睛玩壞的。沒有辦法,不給玩手機(jī),就哭鬧,就不吃飯。”奶奶顯得很無奈。我有個(gè)好友,孫子上小學(xué)一年級(jí),好友周末接到家來,好吃好喝伺候著,但孫子要奶奶陪著玩手機(jī)游戲。奶奶說,不會(huì)玩。孫子居然把好友手機(jī)給砸壞了。如果不是親聞,還真是無法相信。
所以,當(dāng)看到不玩手機(jī)的孩子時(shí),就覺得像大熊貓般稀奇。
九月上旬,單位組織職工療養(yǎng),同事帶了上幼兒園的小寶,我們都叫他弟弟。幾天的行程下來,發(fā)現(xiàn)弟弟有個(gè)最大優(yōu)點(diǎn),就是不玩手機(jī)。我們坐下來休息時(shí),都在低頭刷手機(jī)。弟弟自己找樂子,一會(huì)兒和爸爸互動(dòng)表情包,邊搭配肢體語言,笑啊、哭啊、生氣啊、痛苦啊,讓人忍俊不禁;一會(huì)兒舉起玩具手槍,專注目標(biāo),像個(gè)射擊手,很有范。一會(huì)兒,圍繞著我們轉(zhuǎn)圈圈數(shù)數(shù),扮鬼臉。我們不時(shí)用手機(jī)上小游戲引誘,測(cè)試他有沒有定力。弟弟心動(dòng)了沒,心動(dòng)了,弟弟行動(dòng)了沒,沒有。他只是偶爾瞟上一眼,再看下爸爸,如果爸爸表情是嚴(yán)肅的,他會(huì)給自己找臺(tái)階下,“我才不喜歡手機(jī)呢,我是逗你玩呢。”那一低頭的掩飾,把我們給逗樂了。
我很好奇,問同事,“大人都有手機(jī)依賴癥,何況是小孩,你是怎么教育的,很難得。”同事說:“不玩手機(jī),是我們家的新家規(guī)。”我說:“如果弟弟向爺爺奶奶要手機(jī),都說隔代疼,怎么辦?”“那也不行,家規(guī)就是所有家庭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姐姐是考上大學(xué)后,才擁有人生第一部手機(jī)的。”姐姐榜樣在前,弟弟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有老老實(shí)實(shí)坐等上大學(xué)了。
同事女兒,去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xué),令人羨慕。也難怪,姐姐能上名校,絕非偶然,而是必然。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凡事皆有因果。為同事的新家規(guī),點(diǎn)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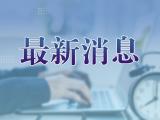


請(qǐng)輸入驗(yàn)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