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quán)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wǎng)站或個人,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鏈接、轉(zhuǎn)貼或以其他方式復(fù)制發(fā)表;已授權(quán)的媒體、網(wǎng)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wǎng)”,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zé)任。
有一篇評論文章稱:讀當(dāng)代小說,讀了十萬字,還沒聽到一聲鳥鳴,也沒看到一片樹葉;還有評論稱:不知從何時開始,植物成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天地里的稀有物種。作為一個讀者和草木愛好者,我深以為然。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不能一概而論。
我書架上就有一本2012年出版的《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作者是阿來,據(jù)說是他相關(guān)博客的結(jié)集。這是我讀過的阿來唯一的一本書,因為書中記述了他在成都拍攝、觀察植物的經(jīng)歷與感受,與我的愛好相契合。阿來以小說家名世,2010年的一場病,拉近了他與草木的距離。入院時病房樓下有一株含苞待放的蠟梅;手術(shù)后,相隔十來天,蠟梅竟成了遲暮美人,只剩下幾縷幽香,在寒風(fēng)中浮動。正是這一樹蠟梅,在冥冥中引領(lǐng)著阿來,讓他的目光,暫時從書卷中移開,投向身邊的草木。他說:“我將它們一一拍下,回去檢索資料,看它們在植物學(xué)上的意義,以前的文人怎么描繪它們,然后書寫植物花事。”這件事成了他重要的日常作業(yè),無論到哪里,草木都是他的追尋對象。有一次他去了意大利,帶回來幾百張照片,其中有認(rèn)得的,也有不認(rèn)得的,他找來《植物志》一一辨認(rèn),確認(rèn)一種,就把它發(fā)到微博上,與人分享,也讓自己高興一陣子。單就這一點,他和我們這些草木愛好者,算得上是同好,但放到作家群體中,就顯得比別人技高一籌了。
我家里還有另一本叫《植物記》的書,作者李漢榮,是個寫散文的。我長期訂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雜志,自己偶而也在該雜志上發(fā)點短文。我在這本雜志上常常讀到李漢榮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寫他家鄉(xiāng)的花花草草的,他的這本書,也是《散文》雜志策劃出版的。李漢榮與阿來不同,他一邊看著草,一邊想著詩:“這泛綠的青草可是從白居易的詩里生長出來?”“我看見了車前草,還是在《詩經(jīng)》里那么優(yōu)美地?fù)u曳著。”“看韭菜排列得那么整齊,像杜甫的五律……”李漢榮的文字,充滿了奇思妙想,讀來很是賞心悅目。而李漢榮自己,卻是一本正經(jīng),他認(rèn)為世上沒有虛偽的植物,沒有邪惡的植物,沒有懶惰的植物。“與植物呆在一起,人會變得誠實、善良、溫柔并懂得知恩必報。”
諸多小說的環(huán)境書寫中,也會語涉草木,但通常是作為背景素材,像繪畫中的大寫意,或一筆帶過,或恣意揮灑,但認(rèn)真的寫作者并非如此。2002年我在西安,下了班就讀《白鹿原》,有一天讀到第三章,白、鹿兩家換地,這坱地與鹿家原有的地隔著一垅埂,那埂上長著野艾、馬鞭草、菅草、薄荷、三棱子草、節(jié)兒草、旱長蟲草(牛筋草)等七種草。當(dāng)時我腦子里浮上來一個疑問:這是泛泛之筆呢?或是實寫?便托人引我去拜訪陳忠實。只見他爽朗一笑:老程,不如你抽空去白鹿原看看。到了雙休日,我真的讓司機陪我去了那里,按書中給出的方位,在灞河灘靠西的一側(cè)搜索。因為是秋季,除了書中那七種野草之外,還拍了好幾種其它草木的圖片,腦海中的疑問至此便煙消云散了。回來的路上我想,這就是大師與眾不同之處吧。
安徽的許輝,前幾年出版的散文隨筆集《人人都愛在水邊》,書中總共出現(xiàn)九十三種草木,可謂樹木琳瑯,芳草萋萋,其中以蘆葦、楮樹、油菜、小麥、灰灰菜、扁豆、牛筋草、薺菜、毛谷谷草(狗尾巴草)、荷花、蒲草等亮相最為頻繁。許輝筆下的草木,沒有奇花瑤草,都是自然界里草根中的草根。許輝在書出版之前,曾當(dāng)面向安農(nóng)大一位植物學(xué)博士討教,請他為自己筆下的草木,作技術(shù)層面上的把關(guān),這種做法,這樣的精神,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當(dāng)然并不止上述幾位,葦岸《大地上的事情》與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就被公認(rèn)為是從莊稼地、從荒野中冒出來的文字。翻閱他們的書,我往往分不清書頁里生長的,究竟是一點一橫長的文字,抑或是一花一世界的草木。作為一個讀者,每每讓我心旌搖曳。
世界太堅硬,草木軟人心;萬事有套路,花草自純真。所以我要說,倘若草木不在場,無論什么樣的文字,也感動不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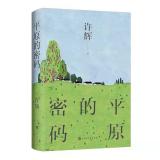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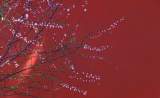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