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夏日悠長,適合讀長篇小說,慕名找來孫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圖》,一氣讀完。既滿足了對這位先鋒小說家“紅色敘事”的期待,也彌補了自己的一個遺憾。
去年5月底,原計劃去廣東汕頭、福建龍巖等地采訪中央蘇區紅色交通線,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千里江山圖》寫的就是這條從上海繞道香港經廣東等地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線。小說以1933年設于上海的黨中央機關的戰略大轉移為背景,以與之相關的代號為“千里江山圖”的行動為題,展開了一個驚心動魄、刀光劍影的地下斗爭故事。孫甘露的文字自是沒的說,草蛇灰線,伏筆千里,構思縝密、筆法細膩。他用文字將散落于那段歷史塵埃中的理想主義者和行動者一一找尋,重新聚起他們的精神和血肉。
孫甘露謀劃這部小說,已有數十年。在2018年的一則新聞中,就有將要出版《千里江山圖》的信息:這部小說關乎《千里江山圖》,也關乎一個男人。大意是,在錯失一生中最珍貴的感情之后,男人重新認識女人、家庭、國族之于一個中國人的意義。而今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千里江山圖》,成為孫甘露沉潛20多年后的“轉身之作”,變成了1933年中共地下組織的“千里江山圖”行動。
《千里江山圖》是一幅名畫,脫胎于此的詩舞劇《只此青綠》今年在央視春晚“暴得大名”。未滿18歲的王希孟在宋徽宗的傳授下,不到半年便繪成了這幅山水巨作。不及弱冠,青春逼人,才有這樣的雄心和魄力,青綠明艷,光華燦爛。已過花甲的孫甘露用數十年的時間、近25萬字的篇幅,寫下了十來個人的青春之華,他們是愛人,是兄弟,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亂世行走江山。“千里江山圖”是行動計劃,是接頭暗號,是革命希望。主人公陳千里與弟弟陳千元在診所對話,“你打開窗朝外看看”,“說的是,這些人就是江山。”“千里江山圖”在此合璧。
創作《千里江山圖》,王希孟像用完了一生的力氣,兩年后英年早逝,以后的青綠山水畫無出其右。為了執行“千里江山圖”行動,相繼犧牲的同志有中共上海區領導老方,婦女干部凌汶,中央特派員林石,以及1933年4月4日一起在龍華監獄就義的陳千元、董慧文、李漢、田非、秦傳安、梁士超和衛達夫。最后時刻,衛達夫本來是有機會逃生的,但為了確保行動成功,為了把釣餌直接下到敵人嘴邊,他微笑著拒絕了生還。《千里江山圖》,是王希孟的“天鵝之歌”,也是烈士們用生命寫下的最后的情書——“我們摯愛的只有我們曾經所在的地方,即使將來沒有人記得我們,這也是我們唯一愿意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讀之令人落淚。
在做采訪案頭工作時,我注意到對于在這條綿延3000多公里的絕密交通線上工作的交通員來說,成功就是繼續隱姓埋名,失敗就是犧牲,大多史冊無名。在小說中,孫甘露賦予他們名字,更準確地說是個代號。這是怎樣的信仰力量感召?面對暴風雨,他們內心的洶涌早已平息。“他們說暴風雨即將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這是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句,在小說里數次出現,表明了他們的人生態度。微笑是蔑視,微笑是愛。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參加這個特別行動,沒有一個人喊過一句口號,沒有一個人說過什么大詞,他們勇敢地把生命交付出去,只因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愛,對祖國的愛,對人民的愛。在革命激流中,在犧牲生命前,這些最純質的愛,是用初心壘起的精神豐碑。
孫甘露一改之前慢速度的敘事風格,《千里江山圖》正文被切分成34個小節外加“一封沒署名的信”和兩個“附錄”,平均每節七千字左右,敘事節奏快、短句多、段落短。比如小說結尾,“陳千里再次翻身上船,抹去臉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艙,命令船工把渡船轉向蘇州河方向”,不再多寫一句。而快節奏、大寫意筆法中也不無細膩的工筆,諸如對三頭宴的描寫、對趟櫳門的交代,既呈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對環境氣氛是一種烘托。無論快或慢,寫實或寫意,孫甘露的文字還是一如既往的優雅、精準和凝練。
小說讀到最后,故事有了終章,任務達成,生命消失。再往后翻,附頁是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從龍華犧牲烈士遺物中找到的。信的結尾寫道:“在這個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著你,望著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這些犧牲的年輕人、革命者,他們甚至都沒有戀愛過,但內心是如此的純粹與遼闊。
孫甘露用文字建構了這種比愛情更奮勇的激情,比愛情更磅礴的青春,完成了驚心動魄、慷慨悲壯的《千里江山圖》。他以文學的方式將主題敘事提升到一個全新的藝術高度,在更深層面上致敬了用初心壘起的精神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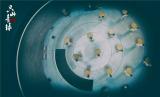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