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早稻熟了,收割的季節到了,我突然懷念起曾在過去“雙搶”中為農民遮陽擋雨的老布大手巾。
老布大手巾比毛巾大得多,一尺來寬,三尺多長;比浴巾要薄要輕,方便耐用。老布手巾的原料就是老布,老布亦稱“土布”,土里生長的、土作坊里軋出的棉花,老式紡車紡出的棉紗,老式織布機織就的布匹,一切與土有關,土里土氣,土色土香,有著泥土的氣息。
如今,大手巾早已淡出人們日常生活圈子多年,人們大多想象不出它的模樣。但在那個年代,大手巾是農民兄弟的標配,到田里或山上干活,大手巾就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到田畈里做活,除了勞動工具外,必帶草帽、黃煙袋、大手巾。草帽遮陽擋雨,黃煙袋解乏,那么,大手巾做什么用呢?
雙搶時節,驕陽似火,炙烤著大地,曬癟了大地的植物,也灼傷著田間勞動人們身上的皮膚。農民兄弟裸露著上身,背上覆蓋著一條大手巾,手忙腳不亂地在大地上串串點點,豆大的汗珠好像從泉眼里鼓起的水泡從皮膚里滲出,只不過這水泡是咸的,滾燙的。衣服濕透,手巾也濕透。農民兄弟把手巾從背上取下,擰干水,擦擦臉上的汗,又將手巾披上背,繼續著永遠干不完的農活。累時,農民兄弟坐在田埂上,點起黃煙袋,哧溜哧溜地吸著煙。田里的水汽,地上的熱氣,黃煙嗆人的煙霧,相互糾纏著,彌漫在農民兄弟的周圍。有時干脆躺在草地上,將大手巾揉成一團,塞在腦袋下權作枕頭,不一會兒,鼾聲四起,因為實在太辛苦了;傍晚收工時,農民兄弟的手巾又成了浴巾,他們將手巾在水里擺一擺,洗凈臉,再擦干身上的臭汗,帶著疲乏的身體向家的方向走去。
鄉村的孩子假期里整天在莊里、田間、山上亂跑,一天下來,臉成了戲臺上的花臉,手成了涂著彩繪的花手,身上的衣服不是沾上草屑就是包滿灰塵。一回到家,若大手巾搭在竹竿上,孩子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扯下來猛擦汗猛揩手猛打灰,自覺形象光鮮多了,只可惜,大手巾卻成了名副其實的抹布。
秋收后,田野里只剩下齊刷刷的稻茬和茬子間泛著清幽幽綠光的花紅草,農民兄弟的大手巾理該束之高閣了吧。但農民兄弟閑不住,一閑身上就發痛。于是農民兄弟和他的大手巾結伴而行,向山里出發,向柴山要柴火,向柴火要油米鹽醋。小屁孩是不關心這手巾揩過什么東西,只掛念,大手巾里是否包裹著什么新奇。農民兄弟挑柴回家還未喘口氣,小屁孩就搶著解開扎成布袋狀的大手巾,有時是山里熟透跌落在地的黑里見紅的毛栗,有時是個頭小但紅艷艷的野杮子,有時是草叢旁生長的蘑菇……這些山里土生土長的果實讓缺乏零食的孩子們嘗到了不一樣的零食風味,童年生活一下子富有趣味。而蘑菇湯的鮮味潤滋著孩子們的口腔,飽醉著孩子們的胃囊,從而對生產野味的大山產生了一種久違的膜拜。
過年時,大手巾會被“冷落”幾天,靜靜地躺在某個角落,因為農民兄弟這幾天才正兒八經地不外出勞作。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普及,種田的勞動強度大大降低,大手巾也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漸漸退出生活的舞臺。但我卻不能忘卻它,關于大手巾的往事,如晨星漸隱時的月亮,始終明晃晃地照亮我記憶的天空……
如今,我時常懷念家鄉的山水,懷念家鄉的風物,懷念同農民兄弟搭擋了一輩子的大手巾。它如同寶物住進心的原鄉,當我想偷懶耍滑時,我就嗅到大手巾散發的勞動味道,這種味道,在我記憶的幕布上,怎么抹也抹不去。
大手巾里有濃濃的汗味,而每一粒糧食都被汗水浸泡過,它告訴我,珍惜每一粒糧食就是尊重人世間的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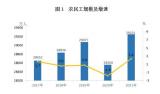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