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最近看脫口秀大會,我在想為啥沒有人講控制型人格和討好型人格的內容,如果我講,就講這個。
20多年前我在高校里工作,有個學生是云南的,具體是云南哪里我忘了,總之說當地的蘋果特別好吃。這學生的父母很疼孩子,入學報到時就是大包小包,還帶著她媽媽做的幾大瓶辣椒菌子,說擔心孩子吃不慣廣州清淡的飯菜。
不知怎么我也跟這名學生家長認識了。我當時只是學校行政部門的一個工作人員,認識我也用處不大。但我完全理解家長的心理,能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給自己閨女多認識一個人,那就是為閨女的前路多鋪一塊磚。我就是這么一塊磚。
有一天,接到來自云南的電話。這位學生家長在電話里熱情地說,剛剛給我買了一大箱蘋果。“新鮮大蘋果,我們這里最好的大蘋果,你吃就知道了。”他說。說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幫忙帶上一趟途經廣州的火車。那趟火車在明天凌晨六點鐘經過廣州,會在站臺上停車幾分鐘,我呢,就要在那個點兒等在站臺。
到底多大的一箱蘋果,他是怎么托到的人,怎么運上了火車,稍微一想都是眼前一黑。凌晨六點,那么四點多我就要爬起來,學校偏僻,那個點兒能不能打到車,多久才能打到車,都是問題,必須多預留點時間。拿到蘋果后,要怎么從站臺搬到火車站外面,然后再打車,搬上車,我的眼前真是黑了又黑。
那是二十年前,沒有什么騎手派送啦,同城速運啦之類的,也沒有相熟的出租車司機,一籌莫展,幸好有一個男朋友,他雖然不情愿卻也責無旁貸地去了。本來那一箱蘋果就是對他的報答,誰知他堅決不吃:“我最討厭吃蘋果。”我想,經此一役,他對蘋果那種莫名的惡感,又增加了幾分。蘋果,太無辜了。
學生家長那邊,我當然也不停道謝:“廣州確實沒這么好吃的蘋果。”我說。
如今回想一陣后怕,我那么感恩戴德,他要是一高興,又給我托運一箱過來怎么辦。
這個事情經常被我回味,因為它足夠典型,又足夠小,所以是一個充滿喜感的煩惱。這個事情的實質其實是,總會有人出于完全真誠的好意,給你帶來他以為的驚喜,但對你來說只是驚而不是喜。同時你也被動地承下了一個巨大的情。
我也沒有辦法拒絕。首先是來不及拒絕,因為我得知的時候,蘋果已經在路上;其次我即使拒絕,他也會認為我在客氣,否則怎么會讓蘋果先上路;第三是,如果我們再熟悉一些,如果我再卑微一些,如果我繼續拒絕,那么,他會對我發出靈魂的逼問:“這蘋果是不是廣州吃不到的?是。既然是,有機會吃到,為什么不要?是不是擰巴?還是怕麻煩?為什么這么怕麻煩?為什么不愿意克服一下困難,過上更好的生活?”
之前每次想起,我的側重點都在這個學生家長身上;但這幾年我的想法有所改變,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問題就出在我卑微的感謝里。
當他跟我熱情地介紹到他們家鄉卓越的蘋果,當時我一定報以了同樣熱情的興趣。那是一種未經思考的興趣,僅僅出于習慣。我太擔心掃了別人的興。我覺得只有表現出興趣,別人才高興。我還擔心如果自己沒有足夠的回應,愉快的氣氛會毀在我手里。
所以,我流露出來的熱情給了他錯誤的引導,當他千辛萬苦給我托運來蘋果的時候,他一定是充滿成就感的:“上次我和你提到我們的家鄉特產蘋果,你很有興趣。”
而收到這箱卓越的蘋果后,我也一定是在電話里熱情地感謝他,贊美它們。同樣也因為:我也只是習慣這種回應。我覺得,如果我不說自己很喜歡很開心,對方就白忙活了,就又掃興了。“讓別人掃興”似乎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令我沒有勇氣做出真實的反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
有時候我們批判別人的控制型人格,很可能是因為自己的討好型人格;有時候我們批判別人沒有界限感,也很可能是自己的反應給了對方鼓勵。控制型人格和討好型人格形成了一對CP,彼此之間互相成就,如果自己堅決地保持自己的界線,對方也就沒有越過界限的機會。
那么,為什么會害怕掃了別人的興呢?自己有那么重要嗎?也許心里真正害怕的是,氣氛一個維持不住,就是人生里的寂寞。所以哪怕是假相,也要高高興興的。討好型人格在別人那里如何我不清楚,在我這里,主要就是把氣氛打發過去,潤滑地打發過去。
但事實并不能如自己所愿。先不說打發了氣氛之后,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額外麻煩,就是你想討好的,也往往討好不了。
我有個朋友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她的前夫有嚴重潔癖,但她很愛他,就一直要求自己按他的標準來生活,不要觸怒他。每天洗完澡,她總是會很注意,把掉到地上的頭發掃到一起,揉成一團撿起來,怕丟在廁所會堵塞馬桶,她就撕一張紙巾,把那團頭發包起來,再帶出去丟掉。如果她洗澡后輪到前夫用浴室,她會特別地再仔細檢查一遍,地板上的積水、頭發絲都清理一遍,肉眼看似乎沒有什么不妥的。
但即便如此,打掃后的她還是會隱隱覺得不安,非常不安,覺得還有哪里出錯,肯定有她的盲點,她的死角,——盡管她左查右查查不出來,但她還是預感到她前夫一會兒黑著臉出來,又指出了她的哪一個漏洞。
果然,她的預感總是成功地變成現實。她前夫的臉,總能如期地黑著,指出諸如紙巾包的頭發忘記丟掉、某件臟衣服忘記收出去放洗衣機,諸如此類的事。久而久之,她覺得一切仿佛是宿命,她怎么努力,怎么希望糾正,都無濟于事。事實就像她前夫斬釘截鐵認準的那樣:你真是邋遢。
她終于發現,自己的邋遢是被前夫創造出來的。有一本勵志小說叫《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面說,一個人的愿望足夠強烈,整個宇宙都會來幫你。沒想到,一個人的擔心足夠強烈,整個宇宙也會來幫它,使你一次次穩穩地做成自己最擔心的事。
神奇的是當他們離婚后,她的邋遢就全然不存在了。起碼她不再忘記把臟衣服收出去、忘記把包著頭發的紙巾丟掉、忘記清理浴室。她很奇怪為什么不需要糾正的時候,自己反而能做得更好。
但即便這樣,得知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有很多人站在她前夫那一邊。因為愛清潔沒有錯,對自己高要求也沒有錯。仿佛她是為了逃避改掉邋遢的習慣、逃避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選擇離婚的。
在我們生活的上空仿佛有些無形的規定,規定正確和錯誤。邋遢和懶散是錯的,整潔和勤快是對的;能吃到大蘋果肯定是好的,吃不到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那名前夫貌似掌握了“正確”的生活方式,其實他掌握的,只不過是對方的討好型人格和弱勢心理。
離婚后她才撥云見月地明白了,生活方式該由自己說了算,沒啥對錯,只要不傷害任何人。邋不邋遢要由自己說了算,即使真的邋遢,那也是小事,覺得自己邋遢、進而覺得很糟糕,那才事大。討好自己比討好任何人都更加事不宜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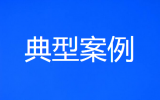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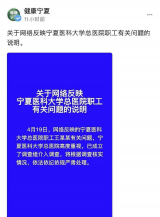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