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在合肥,住進這個小區快十年了。對小區最滿意處是它的綠化,或許這就是當初選擇它的一個重要原由吧,房前屋后草木葳蕤,窗外四時景異,令人賞心悅目。
我在多篇文章里寫過書房窗外的樹,包括樹上的鳥。那是一株銀杏樹,高大婆娑,是我熟悉的樹種。至于南邊房間窗外那棵樹,此前沒有寫過。我不熟悉,也不太喜歡那棵樹。
自以為閱樹無數,對諸多植物都能叫得出名。搬進這間房子后,對南窗外的那棵樹,在很長時間里卻叫不出它的名字。入住是在初秋,說是初秋,其實還是炎夏,天氣熱得很。那時光,草木仍舊一派蔥蘢,看不出衰敗的跡象。南窗外的那棵樹卻例外,過早地散發出遲暮的氣息,稀疏的心形葉子色澤枯澀,葉面不再平整,大多向內蜷曲;葉柄附近,樹的枝干上披掛著一些干枯的扁豆,顏色深暗。于是,我對這棵形容枯槁、神情憔悴的陌生樹種不懷好感,它存在于我眼皮底下,我卻視而不見。
第二年春天,情況有所改變。農歷正月尾,天氣還冷,除了梅花開放,別的花都還沒有睡醒。落葉樹木的枝頭依舊光禿禿的,新葉尚未生發。南窗外那棵不知名的樹是落葉木,我記得在秋天里它比別的樹落葉都早,這會子它還沒出葉,滿樹枝杈。有天早晨,我起床來到窗前,習慣性拉開窗簾,推開窗玻璃,忽然發現窗外裸露的樹枝樹干上,突然有了些紫紅色的星星點點。一時很興奮,覺得這棵樹不是尋常物,它有真性情。春天一到,它便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張開了小口,向春天敘說些如花的語言。那一刻我被這棵樹的率真深深感動,情不自禁地驚叫了一聲:呀,它已經開花了!連續好幾天,我天天站在窗前看它,一天看幾次。那樹枝樹干上的花,越發越多,越開越大,越來越艷。一簇簇,一球球,一堆堆,密密麻麻紫紅的花朵,將樹的枝干團團圍住。樹的枝杈本來傾斜向上,開花之后枝條紛紛朝下低垂,讓人產生一種擔心:這棵樹會不會被自己的美麗壓垮?樹枝們沉甸甸地低垂了大約十天時間,終在一個早晨發現,昨夜風雨讓它們如釋重負,地上落紅無數,如厚厚一層紫紅色的積雪。一時間我心情沉重起來,為那滿地落英,為眼前那棵樹,但又很快走出了那種莫名其妙的情緒,我發現那棵樹本身并沒有那種情緒,它反而輕快起來,樹枝和樹梢都抬起了頭。
有些花開便開了,落也便落了,不會留下花開花落的成果。那棵樹不是這樣,花落幾天之后,樹枝和樹干上便冒出一些細小的“耳朵”,仿佛這棵樹正在側耳傾聽一個季節的秘密。和煦的春風里,“耳朵”們一天比一天放大,漸漸成形,讓人看出那是些細長而扁薄的豆莢。在豆莢長大的同時,還有一樣東西迅速生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那是樹的葉子,春天里,新生的葉子青翠欲滴,富有光澤,洋溢著勃勃生機。
這時,我才想起打聽那是一棵什么樹。樹是開發商栽的,小區物業人員或許清楚情況。有天在樓下見到物業工作人員問起這事,物業人員不假思索告訴我,那是紫荊樹。我猶不信,紫荊花是香港的標志,許多地方都有紫荊花圖案,我見過多次,不是這樣子。不過,提起紫荊樹,我倒想起杜甫的詩句:“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還有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中的故事:“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問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由此,我更加堅定了先前的認知:此木不是無情物,它重情重義真性情,令人自愧弗如。
后來,和朋友出去玩,發現朋友手機上有個聰明的軟件,能識別人間草木,當即下載一個,回到家里,站在窗前,舉起手機朝窗外那棵樹一照,果然手機提示此木為紫荊樹。紫荊樹開花,當然是紫荊花。不過,它與香港區花紫荊花的確不是一回事,那叫洋紫荊,也叫紅紫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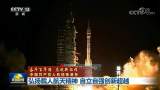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