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家鄉南觀是瀛洲鎮下轄的一個小山村,村里人都姓汪,我堂叔汪珂在鎮小學教書,常帶我去瀛洲玩。那年我八歲,第一次出遠門,很好奇。我們翻過一個小山坡,途經周村,而后是田間小路,曲曲彎彎,盡頭是一條大河,河上架有高高木橋。登上橋,能看到橋頭的水碓,靠河是一個碩大的木制水輪,靠河水推動,日日夜夜,吱吱呀呀,發出震耳欲聾的響聲,老遠便能聽到。若干年后,我與水碓結緣,留下一段情,后面將提到。
過了橋,堂叔說:“到了。”
我抬頭,只見一座高高的門樓,上面有兩個斗大的字:瀛洲。穿過門樓,步入古街,街道用略顯粉紅色的花崗巖石板鋪就,齊整有序,非常壯觀。古街兩側有許多家店鋪,記得,第一家是面食店,沿街而上,還有搖面店、豬肉店、中藥店,以及賣京貨、南貨、布匹和裁縫、鐵匠、理發等店鋪。街上,人來人往,有買有賣,那抑揚頓挫的吆喝聲,震人耳鼓。堂叔是鎮上學堂老師,不時有人呼喚:“汪老師!”堂叔抱拳回應:“早!”一位雜貨鋪老板走上前來,拉著堂叔,步入店堂。老板捧來一杯茶,道:“小店換招牌,借重先生的墨寶。”堂叔接過茶,點點頭:“拙字,見丑。”堂叔寫得一筆好字,古街許多家店鋪招牌都出自他的手筆,贏得一片贊譽。臨出門時,老板抓了一把花生米塞進我的口袋。
穿過人流,走出古街,離瀛洲小學不遠了,路上便能聽到朗朗的讀書聲。記得,學校前面是操場,踏上臺階,走進校門,左右兩側是教師宿舍。再往前,中間是麻石板和鵝卵石鋪成的甬道,兩側是教室。走過甬道,隔著天井明堂是學校的會堂。會堂東側是教師備課和批改作業的辦公室,再往后是廚房和男女廁所。學校師生共有百余人,是鄉里最高學府。堂叔很忙,一到學校,便端起粉筆盒,去給學生上課,把我丟在房間里。堂叔上完課,回到房間,我正拿起粉筆在墻上涂鴉。堂叔見狀,說:“想學寫字嗎?”我點點頭,于是堂叔拿來一塊小黑板,手把手地教我寫字。記得,我寫的頭一個字是“人”。堂叔說,左一撇右一捺,頭頂天,兩腳踏地,做人就要頂天立地。我的啟蒙教育便是從瀛洲小學開始的。
十年后,我考上了宣城師范。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父親因勞累臥病在床,母親忙家務還要照顧父親,祖母年邁,下水碓舂米這份活自然落在我身上。記得第一次下水碓是跟堂嬸一道去的。剛進水碓房時,面對那一上一下飛動的石杵,心里好生害怕,萬一石杵砸到身上,那還得了?堂嬸看我呆呆地站著,便說:“看人家姑娘都會舂碓,你一個男子漢怕什么。”我才發現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也在碓房里忙活。此刻她一手托住石杵,將它掛在梁上垂下的粗繩套上。我不由暗暗驚奇,上下飛動的石杵在她手里竟服服帖帖,好膽大!堂嬸因家里還有小孩,忙過一陣先走了。姑娘瞧我是“生手”,主動過來,教我掛石杵,又教我篩篩子。在她的幫助下,我學會了這些技術活。
干完活,我與她攀談起來。“你是哪個村的?”“周村。”她說,“我還見過你呢。”“在哪里?”“汪老師房間里。”原來小時候跟堂叔去瀛洲玩,她已上學了。堂叔后來調到仁里小學任教,我就很少去瀛洲了,虧她還記得。
彼此熟悉了,于是互通了姓名,我還知道她小學未畢業,因父親去世,輟學在家務農,成了母親的一條臂膀。她落落大方,是個難得的好姑娘。
分手時,她挑著兩籮白米,邁著輕盈的腳步,兩條辮子晃悠晃悠地,消失在蒼茫的暮色里。
我回到家,心里若有所失,向缸里倒白米,竟潑了一地,被祖母數落了一番。于是,我天天盼著去舂碓。終于,缸里白米吃完了,這回不用祖母吩咐,我興沖沖地挑著兩籮稻谷下水碓。不巧,那天碓房里除了缺門牙說話不關風的老太婆,什么人也沒有。我一邊舂碓,一邊到碓房外眺望,可是,哪有姑娘的影子?
暑期結束,我回到了學校。從此,我再沒有下過水碓,那個曾教會我舂碓的姑娘我卻一直還記得,怎么也忘不了。
往事只能回味,夢里瀛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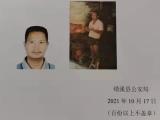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