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幾天以來,我時時沉浸在孫禹《童話與水》《東方芭蕾花鼓燈》這兩本書給我帶來的閱讀喜悅和震撼之中,老實說,除了回憶起曾經聽到他那曲“大江東去”的嘹亮美聲之外,之前我對孫禹的文字沒有任何印象。但讀過《童話與水》之后,我得到了被洗禮、被陶冶的享受,這是一種久違的、并不常見的體驗。
人們都說文如其人,其實文也如生活。只有生活被作家真正感受過,才能化為感人的文字流淌出來。我們看到,孫禹的文字與他描寫的生活貼得是那樣近、那樣緊,幾乎可以說,無一字不浸透他對生活的感知、感悟與感念。在《童話與水》中,無論是對自己成長歷程的回顧,還是對親人、恩師、友人的感念,都來自實實在在的生活長河。60多年的時間旅程,在茫茫的宇宙中,也許連一瞬間都算不上,但是對于孫禹來說,卻是他的全部。是他充滿了被感知的生活的全部精神礦藏。孫禹是一個善于觀察的人,生活的任何蛛絲馬跡,情感的任何波動起伏,表情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別想逃過他大腦雷達的掃描,對生活點點滴滴的細微觀察,都化為了他創作的真材實料,構成了他散文的優異質感。
但同時,孫禹更是生活主動而熱烈的參與者,絕非那種生活賬本兒的被動記錄者,他的散文是對生活的提煉和萃取,充滿了靈動的思考和精益求精的篩選。人間的善與美,惡與丑,真與純,痛與恨,被他收納匯聚之后,以“情”字貫穿起來,將人生中經見的所有起伏跌宕,心路歷程的喜悅或坎坷,穿越了時空,漸次地彰昭出來,構成了流光溢彩的人性交響。
人們都說文學是人學,真正的人學是具體的,體現在歷史的滄桑巨變中,發生在崢嶸歲月的流轉中。孫禹以“人”的尺度構造自己的散文,他始終把發現人的真、人的復雜與人的能動性作為使命,在世事的變遷中反觀人物的命運,挖掘人物內心。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他那位瘦弱的、與失眠相伴一生的母親,對歌劇嘔心瀝血的“媽媽桑”,作為“大先生”的嚴歌平,孫河鎮那個樸實的農民清軒叔,經常靠喝涼水充饑的奶奶,偉大的伯樂瞿弦和,發現他歌唱天賦的吳樹聲,比利時熱心的讓·路易夫婦等等,這些人物的人生歷程,就是最偉大最精彩的人間故事。這些人也許永遠沒有想到自己那些支離破碎的生活,有時候甚至是根本拿不上臺面的生活,會被一位作家寫在書里。恰恰是經由孫禹的發現,這些人物生活的吉光片羽,構成了故事江河里最吸引人的浪花。善于發現生活才算是真正懂生活的人。能夠時常感悟人間愛與溫暖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過的人。孫禹作為人性之不凡當之無愧的發現者,他所自覺萃取和熱情傳播的生活中的人性之美,構成了自己文字最可貴的質地。
孫禹是緊貼人民大地的人,他的性情是熱愛人民的性情,他的真率、坦誠和無私,是擁抱人民美好品格真率、坦誠和無私,在作品中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對美好品性的執著之愛和堅守。他的文字之所以噴涌著熱情與才情,之所以適于朗誦和高歌,在于他和命運展開過搏擊,在藝術生涯中發動過一次次強者般的進攻,是因為有來自燕趙兒女慷慨悲歌基因的強大支撐。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言不合據理力爭,他的人生與文字延續了從遠古走來的北方漢子的精氣神,體現了對偉大祖國和腳下這片土地的深沉之愛。哪怕洋裝穿在身上,國外生活二十余年,都改變不了他作為中國人的赤子之心。他對中國傳統詩文如數家珍、信手拈來般的熟悉,對花鼓燈等中國古人文化留存的深深眷戀,與他從小的文化浸潤分不開,可以說,早已經融入到他的情感方式和思維方式之中。打開《東方芭蕾花鼓燈》,撲面而來的,是他對中國藝術的熱愛,他把自己的命運與“花鼓燈”傳人們的命運聯系起來,去安徽花鼓燈發源地和燈窩子采訪,一次次不辭辛勞,苦惱著他們的苦惱,喜悅著他們的喜悅,最好不過地詮釋了他對百姓對勞動對土地大寫的愛,這種創作就是值得人們學習。(作者系《文藝報》總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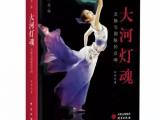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