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那次回老家,發現在大哥家的墻角里,堆放著很多用過的蜂窩煤渣。這些煤渣,被整整齊齊地碼在那里,足有半人來高,很是顯眼。
我問大哥:“放這些煤渣干什么用的?”大哥鼻子里哼了一下,說:“你大嫂收的,像撿個寶貝樣,瞎作弄。”語氣里,明顯帶著一些不屑和不滿。
大嫂正在廚房里忙著做飯。得了空兒,我又老話重提,問她到底做啥用。大嫂習慣性地嘿嘿一笑,說:“沒啥大用,就是舍不得扔掉……”
“既然沒用,那還留著干嘛,扔掉算了,還能騰出一塊地方來。”我說。大嫂又嘿嘿一笑:“話是這么說,這些城里用不上的煤渣,在農村說不定還有用。”
“有啥用?”我追問道。大嫂撩起圍裙,擦了一下手說:“栽花,種樹,墊路,蓋雞糞,都行。你忘了,以前在老圩子里住的時候,家家都用這煤渣鋪路。”
大嫂的話,勾起了我的思緒。是的,幾十年前,我還在農村居住時,村里曾經有一條用煤渣鋪成的小路。那時,在窮鄉僻壤里,能有這樣的路,已經相當不錯了。
記得,當年的村莊里,完全是一個泥土構成的世界,除了泥土還是泥土,村子里找不到一塊磚頭、瓦塊之類的硬東西。土房泥屋,永遠是村莊的主色調。
晴天一地灰,雨天一腳泥。一到下雨天氣,村子里到處是一片爛泥,出門就得和稀泥,弄得大人、小孩渾身上下泥漬斑斑,跟個泥人似的。
后來,村里有人開始用煤做飯。燒過的煤餅渣都派上了大用場,拿來鋪路。先從自家門前鋪起,一點一點向前延伸,最后,把每家每戶都連在了一起。
煤渣路只有一尺來寬,像一條小蛇一樣穿街過巷,蜿蜒曲折,走在上面嘎吱作響,村里人再也不用和稀泥了。我和小伙伴們走在煤渣小路上,像過年一樣開心快活。
上世紀八十年代,村莊整體搬遷到公路邊,家家都住上了樓房、磚瓦房,門前屋后的道路都修成了石渣路、水泥路,以前的煤渣路再也看不到了。
老圩子里都已復墾,變成肥沃的良田。那條曾經的煤渣小路,時常讓我想起,心中總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就像朱自清所說:“有一條狹窄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細小的顆粒,腳踏上去,便發出一種摩擦的噪音,給我多少清新的趣味。”
煤渣路成了我心中永恒的記憶,也成了大嫂念念不忘的回想。這幾年,大哥家的日子早已今非昔比。就拿做飯來說吧,他們家在村子里最早用上了電飯煲、液化氣,但大嫂一直還保留著燒蜂窩煤的習慣。
逢年過節,我們在外工作的幾個兄弟,還有天南地北的侄兒侄女們,老老少少幾十口人,都一起回到大哥家團聚,大嫂就擺開兩三個煤爐,燒水、燉菜、烀臘物、熬稀飯,忙得像陀螺一樣。
大嫂延續多年的燒煤習慣還好理解,可她喜歡收藏煤渣的愛好,卻讓大哥和我們兄弟幾個很是納悶。大嫂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她怎么就舍不得扔掉這毫無價值的煤渣呢?
偶一抬頭,忽然瞥見大嫂斑白的頭發和滄桑的臉龐,我突然明白了:大嫂收藏煤渣的這一愛好,除了說明她的節儉之外,似乎也在表明她的另一種懷舊方式。
大嫂愛好的這些煤渣,其實是對曾經苦難經歷的一種珍藏,也是對逝去時光的一個念想,更是對新生活的一種感恩。
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有獎征集新聞線索,可以是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一經采用將給予獎勵。
報料方式:新安晚報官方微信(id:xawbxawb),大皖新聞“報料”欄目,視頻報料郵箱(baoliao@ahwang.cn),24小時新聞熱線:0551-62396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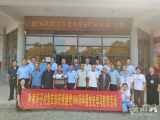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