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從父母家里搬到了壽縣城內東園的一所房子里住,經過三步兩橋往北,在向東幾百米處,東邊鄰近鄭家莊,前后的周圍是一大片菜地。東南方便是壽春報恩寺,城里最好吃的黃心白菜產于這里,又是壽州香草的出生地,到了冬天,這里的鹽硝地長出了最好吃的東園白菜,東為上首,人們又把它稱為上園。
那時我住在幾間不大的自建房子里,位置應是上園的中心地帶,安靜的四周如同身處世外桃源,走出院落,風輕云淡,處處都是菜香。房后是一望無際的菜地,所在地屬于城關鎮永青公社的一個生產隊。我住家的西北處有個石頭堆砌起來的機房,用于抽水澆菜的,機房內一個大深井,機房不大,十平方左右,內有一個大井,井很深,架起的兩根長木頭上,固定著抽水機。我常早晨或傍晚的時候,聽到抽水時的機器轟轟聲,便漫步過去觀看,常有淳樸的菜農在那里忙碌著,見到我微笑招呼,有種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的感覺。大井旁邊有方形的糞池,過去叫農家肥,抽水時菜農不斷地把池中的糞舀到水中,隨著水流向一塊一塊的菜地中,長此以往,這片土地很是肥沃,這也是上園菜地的精髓和獨特之處。
那時候孩子小,下班后拉她閑走,家院東南方一條土路轉彎抹角可通往東內環,而人走得稀少,兩邊長滿了野草,有一種不知名的藤蔓,成熟的夏秋季節如同爬山虎一樣伸出綠色枝頭,長出的果實如枸杞一般大小,由綠變紫,人們都叫它老鴰眼珠子,這俗名也很形象。那時東園靠近城墻邊上又長著許多的野生枸杞枝條,紅色小果點綴在雜草間,而在菜地邊的空處也掛著絲瓜和南瓜的果實。
東南方向的報恩寺院墻后,是種植香草的一塊地,曾經那里的草香飄揚百里,引來宋太祖趙匡胤的戰馬跑來吃草的地方,那里的香草為何好呢,這與唐朝貞觀年間建的東禪寺有關聯,報恩寺里的香火旺盛,千百年來的香灰從寺里后墻清掃出來,灑入墻后的土壤里,長此以往,泥土與香灰相融合,肥沃了園地,滋生了香草的品質。
過去上園的菜地很大,北到城河子岸邊,也就是如今的熙春公園大塘,西邊到老一中東墻外,西南邊到了清波蕩漾的灑金塘處,那塘里蘆葦搖曳,水鴨成群,景色旖旎;西北方一直延伸到建于宋代的東岳王廟的高墻外。
上園菜地里種植的不僅是黃心白菜,還有蘿卜、辣椒、韭菜、冬瓜和西紅柿等四季的各種蔬菜,都是純天然的,沒有化學入侵,古時候能夠滿足半個城人們的蔬菜需求。而這塊土地長出的青蘿卜是可以與水果媲美的,從土壤里輕輕拔出來,菜農大姐就用手指甲從頭到尾剝去整個蘿卜皮,嘗一口,甘甜而微辣,肉質酥脆,算是蘿卜里的上品了。菜地里的西紅柿則是紅潤透亮,如少女般的臉蛋,味道軟甜,夏季的時候常常看到一群頑皮的孩子們,穿行菜地間,偷偷摘幾個,跑到塘邊洗一洗,大口而吃,他們流在嘴邊的紅色印跡,就會感受到那種酸甜的沁人心脾的味道了。地里還有嫩芹菜,桿細翠綠,開水燙一下就可以涼拌,清脆爽口,僅此一盤就能喝下二兩小酒。
到了冬天,就是上園白菜的天下了,一場白雪飄過,黃心白菜每棵體格壯碩,大而圓滿,像個富家子弟。淺金黃色的菜心,遠遠地閃著誘人的光,摘取回去,配上牛羊肉燒菜,是上等首選,味甜,莖絲鮮嫩且不纏口,入口即化,既無酸味也無青氣,是小城以外白菜無法相比的上品。
那時的我,回到家,常走在上園的菜地埂上,與幾棵歪脖子的老樹一起站在風中,聞著黃心菜的氣息,看著麻雀們跳躍在枝干間,聆聽著東邊鄭家莊的草房里白鵝的歌聲,那土埂上深一步淺一步的腳印,老鄭家大院里的雞鴨也都散放了出來,藏入寺后的一片叢林中。
時光如煙,白菜的種子也一代代傳承下來,如今的上園也已漸失原有的模樣,那土井,那水池,那一塊塊的小方格菜地,那菜農的憨笑,都像一幅幅畫圖留在了腦海中,留在記憶里,如美好的味蕾,韻味長久。上園的版圖已經成了縮影,白菜也最終沒有競爭過香草,香草園成了主人,也沒有月季那么幸運,老一中的后墻外變成了月季園。
如今我早已搬離了那里,但每到入冬,想起在那淡泊而悠遠的時光里,想起上園的白菜、蘿卜、西紅柿…,我就會到北街菜市場逛逛,尋找那曾經熟悉的老東園菜農的身影,總會發現攤位上那稀缺的白菜,買些回家去,品嘗記憶里深藏的美好。
王曉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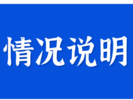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