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有個女孩子看我經常寫阜陽,特地從合肥跑過去。下了車,她問當地人哪里有好吃的,當地人說,“liufang有個小吃街”。她就想著,“liufang”具體是哪兩個字呢,是“六坊”嗎?后來她又通過微博私信這樣問我。
我啞然失笑,哪有這么古雅,就是“阜陽市第六紡織廠”的簡稱而已,這地方我曾經再熟悉不過,后來就隔著一段距離,聞聽它的衰落以及以各種方式再度繁華,比如說,變成這著名的小吃街。
我媽是六紡的老工人。她十八歲那年,六紡到他們村去招工,和我姥姥頗有些芥蒂的我姥爺的族人,叮囑村干部,不要把表格給我媽。后來不知道為什么,那村干部偷偷塞了一張表格給我媽。
多年后村干部進城打工,我爸幫他謀了個看大門的差事,現在他成了正式工,有了養老保險,勿以小善而不為這句話實在對,你不知道惻隱之心一動,會埋下怎樣的伏筆。
但是我媽剛來到六紡時是傻眼的,她在農村雖然缺吃少穿,卻落個自由自在。到這里一天八個小時,不能有片刻掉以輕心,像坐牢似的不說,那工作也著實辛苦,在紡織機前跑來跑去,我小時候就常聽我爸感嘆:“你媽一天最少要跑六十華里,也就是三十公里”。
環境也很差,機器聲隆隆,當面說話都得扯著嗓子,毛絮亂飛,到了夏天,沒有降溫設施的車間里,更是酷熱難當,我媽由不得在心里對自己說,完了,掉坑里了。
可也不帶再回去的,回去讓人看笑話嗎?只能咬著牙朝下做,直到近二十年后,她得了肺病,才從紡織車間調到檢驗車間。
 紡織女工老照片(網絡圖)
紡織女工老照片(網絡圖)
即便如此,那時的六紡還是讓多數人羨慕的所在,收入好,福利也不錯。我媽進廠后就分到一室一廳,之后她結婚,生下我和我弟,加上我爸我奶奶,我們一家五口人,棲身于那三十平米的空間里。
我五歲之前都住在那里,整天跟著一群孩子在偌大的宿舍區跑來跑去,不知道是我動作慢還是人緣差,動輒他們就跑得無影無蹤,我一個人呆呆地站著,感覺到被排斥的失落和委屈。
有時候,我終于跟上他們,從我家住的宿舍區邊緣跑到深處。那里有好幾排筒子樓,我們從黑暗的這一頭鉆進去,路過放在走廊上的各種煤球爐子和鍋灶,躲過影影綽綽的身影,再從光明的那一頭鉆出來,感覺非常魔幻,像是穿過一個魔法城堡。
我多么羨慕那些住筒子樓的小孩,盡管我爸媽一再說,我們家的房子更好,我還是覺得筒子樓更魔幻,住在里面的人,聲息更相通,用現在的話說,更有一種集體主義的樸素浪漫。
六紡的各種設施也很全,比如澡堂。我家搬走之后有很多年,我還是經常到六紡澡堂去洗澡,感覺比外面的澡堂客源單純,因此更干凈,再說廠里還經常發澡票。
檢票口賣點小雜貨,梳子搓澡巾香皂袋裝洗發水之類,也賣橘子汽水,洗澡出來,來一瓶橘子汽水,是無上美味,瞬間彌補了被蒸發的水分。如果是冬天,那一絲涼涼的清甜,可以抵達從上到下所有神經末梢。
還有電影院,我在六紡的電影院看過《筆中情》,講書法家趙旭之的愛情,剛才百度了一下,這電影居然是在《西游記》里演唐僧的遲重瑞和演小白龍的王伯昭主演的。
看過唐國強主演的《孔雀公主》,潘虹主演的《杜十娘》。我奶奶大愛《杜十娘》里的臺詞,有時候在陽光下做著針線活,也會悠悠地念出一句。
 《杜十娘》劇照
《杜十娘》劇照
我奶奶這做派有點抓馬,在我之前,她已經有了十來個孫輩,但她似乎依然沒習慣做個祖母,不會像我姥姥那樣,會時不時塞給我一點零花錢,把好吃的都省給我。
我奶奶是自我的,她一輩子心里都住著一個少女。我整個童年都與她不睦,但她也不能說對我全無饋贈,她對于帶有戲劇色彩的一切的愛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我還記得,她掛在嘴邊的那些民間傳說、戲曲段落,豐富了我幼時的精神世界。
最初的童年陰影,也是在六紡留下的,廠里有個女工被高壓線打死了,似乎是工傷,在廠里舉行了規模極大的葬禮。我奶奶帶著我前去圍觀,有一個女人放聲嚎啕,我奶奶說這是逝者的姐姐。一直到現在,我從高壓線旁邊走過,還是膽寒,即便知道,并沒有那么不安全。
我五歲之后,我爸單位終于分到房子,全家從六紡搬離,但那間小房子還屬于我媽,我媽上夜班之前,或是下了中班之后,會去那里休息。后來我姥姥進城,也住在那里,所以我還是常去六紡,隨著我逐漸長大,理解力增強,在這里,我對生活有了更多認知。
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有六紡人被派到伊拉克工作,這是美差,當時廠里工人月薪五六十塊,到了伊拉克,一兩年間,就能榮升為“萬元戶”。但是,不是有句俗語嗎,男人一有錢就變壞,我媽一個姐們的丈夫從伊拉克回來就提出離婚,姐們一番偵查,發現他有了小三。
那段時間,那間小屋里,每晚會坐滿我媽的女同事,她們義憤填膺,休戚與共,眾口一詞地痛罵陳世美,我那時才發現,這些看上去平凡的阿姨,原來有著如此豐富的詞匯,精妙的表達,在花樣翻新的咒罵中,她們的面容熠熠放光,從不曾如此美麗。
其中有個晚上,她們又一次地在小屋里討論得水深火熱,忽然,有人注意到窗外出現一張黑沉沉的臉,是那個“陳世美”。“秦香蓮”走了出去,他們一起消失在夜色中。屋里的人都有些沉默,然后,互相詢問:“我剛才沒說什么吧?”“我也沒說什么。”
魔法消失了,現實感讓激情蕩然無存,夜一下就很深了,她們的臉上有了一絲絲破敗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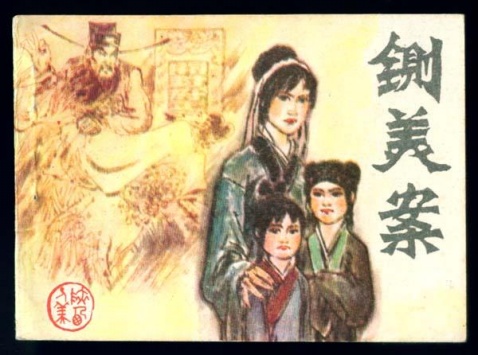 《鍘美案》
《鍘美案》
我總是周末去,周一早晨坐廠車上學,廠里有好幾輛車將廠區的學童送到四面八方,漂亮的大巴車車身上印著三個字,有幾年我念成“哈雨演”,后來才知道是“哈爾濱”。我姥姥總是將我送到車門前,有時還會紅了眼圈,雖然分別不過一個星期,但我姥姥不是感情熾熱嘛。
這種熾熱是一種雙刃劍,一旦她發現被背叛就絕不原諒,我讀初中時,有次回六紡找當年的玩伴,沒去我姥姥家,怎么就那么巧被我姥姥隔窗看見了,隔著一條街,她來不及追趕我,當天晚上,就跑到我們家,把我大罵一通。
好的,說說我去找的那位玩伴,她比我大幾歲,是個文學愛好者,能背《紅樓夢》里所有的詩詞,我到現在也背不下去,也不打算背下來。
她還能背許多唐詩宋詞,尤其愛好李商隱,同時她是一個體育健將,扔鉛球擲標槍全校第一。她生得也美,身材纖長,她有個姨媽特別疼愛她,花很多錢打扮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她穿了一條粉色的真絲緞裙,像個模特一樣飄飄欲仙地和我走在六紡的大街上,引得不少人回頭。
那時,我覺得她從頭到腳都充滿了優越感,追她的男生也很多,然而她中學畢業之后,還是和大多數六紡子弟一樣去了紡校,畢業后可以進廠,得到一個鐵飯碗。
也有人對我媽說過:“你真傻,怎么不讓你閨女上紡校。”我媽說,她從未想過讓我上紡校,她累了這一輩子,還不夠嗎?再說,在我們家,育兒這件事歸我爸負責,她不想操太多心。
女伴也當了兩年工人,那兩年她迅速發胖,她苦著臉說:“沒辦法,我不吃跑不動。”我就此對過勞肥這個事有了了解。后來廠里的業務每況愈下,女伴下崗,跟她的丈夫去街頭賣小吃,我聽到這個消息時,震驚之極,無法想象當年那個詩情畫意的女孩,會這樣步步走低。
好在,又過了一些年,我聽說,女伴的生意好得不得了,開了幾家分店,很多人從外地驅車而來,就為了去她的店喝一碗“咸馬糊”——吾鄉的一種特色小吃,她現在,在阜陽的餐飲業已經很有些名氣了。
你看,喜歡《紅樓夢》愛背《古詩詞》的女孩運氣不會太差吧。
 《紅樓夢》書封
《紅樓夢》書封
我成年之后很少再去六紡,我媽那間小房后來被拆遷了,補償了一套兩室的新房,給了我弟弟,有天我弟弟一高興,把那個房子給賣了,我和六紡的緣分也斷了。有時經過通向六紡的路口,會朝那邊望一眼,成排的樓房,像海市蜃樓一樣浮現在那里,但都與我無關而了。
二十三歲,在我徹底離開小城之前,有熟人請我吃飯,約在六紡,說是原來靠近廠區的一排門面,現在做成了酒吧街。
我赴約而去,看見一個個裝修得挺洋氣的門臉,風情得有點套路感的老板娘。我坐在其中一個包廂里,想起當年,墻的那一邊有許多個車間,終日機器聲轟隆。我曾經進去過一次,像別的女孩子那樣給媽媽送飯,那天電閃雷鳴,一個炸雷打下來,我手里的飯盒哐當落下,我也滑倒在地,不由大哭起來,我媽的同事路過,將我扶起,混亂中,我遺失了腳上的涼鞋袢兒。
她帶著一瘸一拐的我走進車間,跟人介紹:“這是大個子的女兒”,我媽大概一米六七,在廠里已經有“大個子”的名聲,可見中國人這些年真的長高了。沒有來得及趕回家吃飯的我媽看到我很高興,看我這么慘又很心疼,用個瓷缸子打來冷飲,不過是冰鎮糖水,工人勞保飲品,但是在沒有冰箱的當年是個稀罕物,我覺得那一刻的我媽比平時慈祥,也自此覺得車間是個美妙的地方。
吃完那頓飯我就去了省城,其間十多年,不再聽到酒吧街的消息,倒是有一次我問家人哪里有小吃,他們都說六紡。
于是某個早晨,我特意驅車來到六紡,物也非人也非,筒子樓不再,熱鬧的車間已不再,我媽媽那些工友的歡聲笑語已不再,含著淚把我送上大巴車的姥姥也不再,那些玩伴,也像散落的花兒,流落四方。
然而,在這樣一片土地上,還有有一種熟悉的氣息圍繞著我,讓我恍惚,幾乎要掉下淚來。我像個沒頭蒼蠅似的走來走去,走來走去,看見墻,看見墻上的宣傳語,好像吃了一些小吃,但是你要問我吃的是什么,我真的,一點也記不清了。
 作者 閆紅 (未經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權,不得轉載。)
作者 閆紅 (未經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權,不得轉載。)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