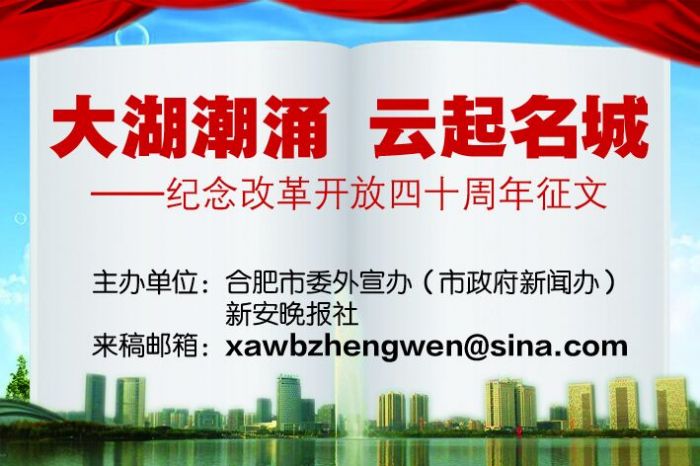
關(guān)于合肥,我老父親最反感的一句話就是“以前的合肥是個(gè)小縣城。”父親說(shuō),那些人根本不了解合肥的歷史,過(guò)去有一種說(shuō)法叫做“南宣北合”,“宣”是宣城,“合”自然就是合肥。
我小的時(shí)候,住在小馬場(chǎng)巷和七桂塘之間的居民區(qū)里。房子是父親單位分的,但與那些老舊的宅子沒(méi)有什么區(qū)隔,所以出入方便,小小的人兒時(shí)常會(huì)獨(dú)自外出“探險(xiǎn)”。也許是小的原因,感覺(jué)合肥城真是很大,怎么也走不到邊。我說(shuō)的“邊”,是指環(huán)城馬路,過(guò)去的老城墻。
在老輩們看來(lái),過(guò)了環(huán)城馬路就是城外了,事實(shí)上也是如此。盡管環(huán)城馬路之外也有機(jī)關(guān)單位,但似乎還是以大中專(zhuān)學(xué)校、科研院所和工廠為主。記得我為數(shù)不多的幾次去南七,都是到工廠那邊的親友家串門(mén)。因?yàn)樘h(yuǎn),好像還在那邊住過(guò)兩次。
還去過(guò)五里墩,很大的農(nóng)貿(mào)市場(chǎng),不是很清楚是否屬于趕集。上世紀(jì)70年代開(kāi)始,越來(lái)越多的機(jī)關(guān)單位往老城外搬,因?yàn)殡m然是城外,但可以有更大的土地,辦公樓和宿舍可以一并解決了。于是,合肥城像攤大餅一樣向四周散開(kāi),我們家也隨著這個(gè)節(jié)奏,搬到了城外的梅山路(現(xiàn)在的蕪湖西路)。
1977 年的梅山路,沒(méi)有路牙,沒(méi)有下水道,更沒(méi)有快車(chē)道、慢車(chē)道、人行道,大家都擠在一條不寬的柏油路上,晴天有灰雨天有泥,兩邊都是黃土裸露的高坡。在與金寨路交口的西北角,甚至還有一片墳區(qū),抄近路時(shí),便會(huì)在一個(gè)個(gè)或大或小的土包間繞來(lái)繞去。春天里,陽(yáng)光很好,草木茂盛,竟然有些田園風(fēng)光的感覺(jué)。
變化,似乎就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開(kāi)始的。修路,種樹(shù),蓋房,梅山路越來(lái)越像那么一回事了,越來(lái)越多的人們來(lái)到它的周?chē)?jīng)商、生活。與此同時(shí),城市化建設(shè)的腳步一刻不停地行進(jìn)著,直到有一天,家門(mén)口的一條高架橋,讓老城與政務(wù)新區(qū)之間的距離變得不再遙遠(yuǎn)的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變得如此之大。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一個(gè)個(gè)新區(qū)建設(shè)起來(lái)了,尤其是濱湖新區(qū),直接將城市推進(jìn)到了巢湖邊上。合肥變得很大,大到連老合肥人都會(huì)摸不著路找不到北了。
城市大了,人們住得開(kāi)了,自然會(huì)面對(duì)一些新問(wèn)題,比如交通,比如購(gòu)物,比如難以割舍的老城情結(jié)。對(duì)于這一點(diǎn),我是很有體會(huì)的。我的一位朋友在搬到政務(wù)新區(qū)后多年,一直都是回到老城里原來(lái)的家門(mén)口理發(fā)。而我在近三年的時(shí)間里,需要從南一環(huán)以南的家,坐車(chē)到北二環(huán)以北的單位上班。在一次次顛簸的懊惱中,我漸漸體會(huì)到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與代價(jià),理解那些大城市里人們的辛苦與無(wú)奈。
好在,這一切都在改變。
慢慢地,人們發(fā)現(xiàn),一個(gè)又一個(gè)商業(yè)綜合體出現(xiàn)了,吃喝玩樂(lè)購(gòu)物,都可以在距離自家不遠(yuǎn)的地方實(shí)現(xiàn)。而地鐵的出現(xiàn),則讓距離變得不再那么可怕。的確,大城市帶給人們應(yīng)該是更多的機(jī)會(huì)和享受,否則要它有什么意義。
物質(zhì)需求滿足了,人們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們要看、要買(mǎi)紙質(zhì)書(shū),他們要參加一些可以面對(duì)面交流的作家與讀者的見(jiàn)面會(huì)和文化沙龍。于是,社區(qū)圖書(shū)館出現(xiàn)了,書(shū)香濃郁的茶吧、咖啡屋出現(xiàn)了。近兩年,一間間高規(guī)格、高品位城市閱讀空間的建成,讓眾多市民切實(shí)感受到文化的滋潤(rùn)。
當(dāng)我徜徉在一個(gè)個(gè)商業(yè)綜合體,或者在一間間城市閱讀空間的書(shū)架上取下一本書(shū)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不再糾結(jié)于合肥到底是一座小城還是一座大城市,我想得更多的是,這座城市的人,是不是已經(jīng)具備與之相符合的胸襟和素質(zhì)。相比于建設(shè)起一座座高樓大廈,人們精神境界的豐富與提高要困難得多,與其在看得見(jiàn)的數(shù)據(jù)上角力,不如在看不見(jiàn)的軟實(shí)力上下功夫。畢竟,人們更看重的是全國(guó)最?lèi)?ài)書(shū)的城市、充滿小資和文藝范的城市這樣的評(píng)價(jià)。
今年 7 月,《中國(guó)青年》雜志用幾乎整本的篇幅對(duì)合肥做了全方位的報(bào)道,主題為:“青年托付夢(mèng)想的城市:‘養(yǎng)人’的合肥做對(duì)了什么?”該雜志社社長(zhǎng)、總編輯皮鈞,在卷首語(yǔ)里寫(xiě)到:“今年以來(lái),當(dāng)很多城市在大張旗鼓‘搶人’的時(shí)候,有一個(gè)城市在靜靜地‘養(yǎng)人’,這就是合肥。”通過(guò)“青年人的夢(mèng)想,依托在城市的文化根脈上”“青年人的夢(mèng)想,依托在城市的人才成長(zhǎng)上”“青年人的夢(mèng)想,依托在城市的胸懷品格上”幾方面的論述,皮社長(zhǎng)得出結(jié)論:“總之,青年人最看重的是一個(gè)城市的態(tài)度。”在文章的結(jié)尾,皮社長(zhǎng)說(shuō):“因此,每一個(gè)有夢(mèng)想的青年人,都應(yīng)該來(lái)合肥看看;每一個(gè)有思考的人,都應(yīng)當(dāng)研究一下這個(gè)城市究竟做對(duì)了什么;感受一下這里的態(tài)度,這里的味道。”
吸引人,留住人,養(yǎng)好人,應(yīng)該是一個(gè)大城市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zhì)。我想每一位生活在合肥這塊土地上的人,都要好好地思考一下,合肥做對(duì)了什么,未來(lái)我們還應(yīng)該怎么做。
我想,這座城市的每一個(gè)人的身上都有一份責(zé)任,以踏實(shí)有效的工作,讓城市更為繁榮強(qiáng)大;以源自?xún)?nèi)心的言行舉止,讓城市變得更為文明寬容。
百年之前的“南宣北合”,只是就一省之內(nèi)而言,如今合肥人要做的,是要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為自己的城市掙得一個(gè)理想的位置和狀態(tài)。
大城也好,小城也罷,不在面積,而在于胸襟。





請(qǐng)輸入驗(yàn)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