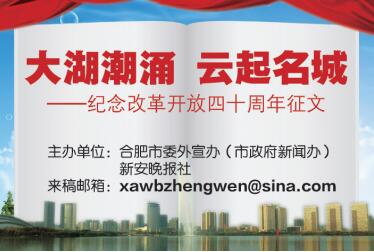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訊 我棲居合肥已近四十年,屈指算算,搬家竟達七次之多。在家庭基本組合紋絲不動的情況下,居然如此折騰,有點奇葩吧?我是徽州“土著”,顯然沒有吉普賽人的流浪情結;向往“詩和遠方”嗎?好像也沒那么浪漫。
“家”的概念,初始于單位筒子樓里的陋室一間。盡管常常尿臊(對面是公共廁所)與飯香齊飄,我一段時間里還是相當心滿意足。后學校蓋房,分我一套兩室兩廳的居所。時為1985年,這是何等的超級福利呀!天下難覓這樣的好單位,我怎能不死心塌地,“從一而終”呢?
那年岳父從黃山老家來,里里外外看了看,笑瞇瞇地說:你們可以在這里住一輩子了。他的意思當然還包括那被稱為“四十八條腿”的家具:五斗櫥、大衣柜、碗櫥……都是用徽州大山里的上好木材打的,用土漆漆得锃亮,下傳三代都用不壞。
房子就坐落在黃山路上。這條路當時細細長長,兩邊野草萋萋,適合談情說愛,尤其在皎皎月夜。我與妻子倒是經常在晚飯后很世俗地來來回回,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勾畫明天的生活與未來的日子。月亮依舊在白蓮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內容則從柴米油鹽,逐步過渡到冰箱彩電。當然,這樣晚風吹拂的時光,也適合談談搬家的事情。一個城市的成長有諸多指標,在吾國,高樓林立恐怕是不可或缺的吧?一個家庭的成長內涵或許豐富得多,“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這話在一段時間里耳熟能詳,時不時地搬搬家,“打幾槍換一個地方”,也是蠻有成就感的!
就這樣,搗騰了四五回。歲月,在一次次的“挪窩”中留下了年輪。在我們家庭的編年史里,一般是以搬家作為基本的記憶單位,與孩子的升學階梯(幼、小、初、高、大)交替使用。每次動作,無非都是樓層、面積、地點的流轉,歸根結底都是使用權的變化而已。昨日窗含四月柳,今天門開臘月梅。悲催的是那“四十八條腿”,幾乎被淘汰殆盡。看到它們一個個地被“掃地出門”,我難免戚戚;可一想到光明電影院、淮上酒家、工農兵紡織品商店,多少又有些釋然。
當我完成第六次搬家后,合肥拉開了大建設的序幕。這個不起眼的中部城市,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就此轟轟烈烈,日新月異。黃山路更寬更直更靚了,兩邊的住宅小區亦如雨后春筍,拔地而起,看得我眼熱心跳:搬來挪去,怎么著也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呀!70年產權,足矣。
于是一路向西,樓盤逐個看去,直抵大蜀山下。某小區里,有同事新買的房子。我被慫恿著更上了一層樓。踏上寬敞的陽臺,映入眼簾的竟是一汪清亮的大水,合肥城區唯一的一座山在西側不高不低地矗立著。一問房價,四千五一平,這幾乎是本埠當時的最高價了。囊中羞澀,我猶豫了。此刻,兩只黑乎乎的水鳥,像是事先有約地從水邊的蘆葦叢中呼啦而出,
貼著水面優美地劃出幾個大大的弧圈。有人說這是野鴨子,棲居這里好久了。我激動了,幾乎是未加思索地脫口而出:這房子我買定了。言之鑿鑿,第二天就交訂金,然后四處借錢,簽合同。售樓小姐驚呼:沒見過這急性人,像在搶房子。三個月后,房鑰匙就掛在褲腰帶上了。
我不知多少次憑窗遠眺,把欄桿拍遍。雖沒有“把吳鉤看了”的豪氣干云,卻也充溢著“風景這邊獨好”的賞心悅目。當然,夾雜著房價見漲的竊喜,盤算著賺了多少銀兩;也目睹著城市向西邊的擴張與發展,豐富著“高新區”這個域名的內涵。這一住,就是10年。中間我也動過心思:傾其所有,去換一套帶院子的宅子,更接地氣,種兩畦蔬菜,植幾株修竹……
然而,我實在舍棄不了這塊“風水寶地”。試想一下,我大合肥11408平方公里的范圍內,還有何處能如此集聚著“真善美”在方圓不到兩公里的地面上?
“真”,科學也,這里有中國科大先研院、中國聲谷、中電科 38 所等科研單位;“善”,則有華東最大的單體寺院——開福寺,它依山而建,氣勢宏偉,還有晨鐘暮鼓,香火繚繞;“美”,自然就是大蜀山與蜀峰灣構成的湖光山色了。我喜歡在黃昏時分倚窗發呆。落日將沉,像個圓圓的紅球,很溫和地掛在起伏不平的山脊上,鑲起一道亮亮的金邊。天清氣朗,正北面的湖水微漾,夕陽如巨筆把天宇涂抹得晚霞如醉,五彩繽紛。不經意,滴下了一點點到湖里。滿湖生金涌銀,無限璀燦。
第八次搬家終究未遂。
(□合肥 許若齊)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