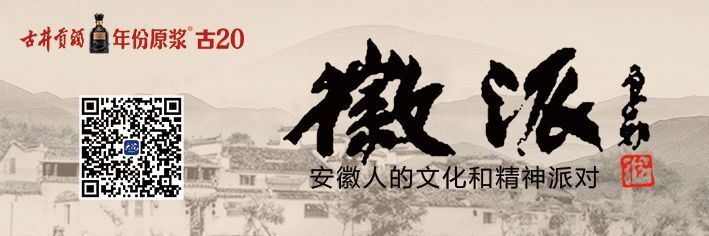
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新聞訊 著名手工紙研究專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手工紙研究所所長湯書昆教授,19日下午做客由古井貢酒年份原漿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欄目,徽派走進湯教授主持的手工紙實驗室,而湯教授也與徽派的觀眾暢聊自己十多年來對中國手工造紙的田野研究心得,并現場向徽派觀眾展示了自己和團隊近些年的若干田野調查成果,以及殊為珍貴的多民族手工紙樣本。
背景:研究手工紙與中國科大的因緣
 中科大手工紙研究所所長湯書昆
中科大手工紙研究所所長湯書昆
徽派:湯教授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和傳統工藝相關的手工紙的研究所,關于它的一些背景故事。
湯書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主體是理科或者叫自然科學研究,加上一部分工程,或者說技術科學的研究。但是,對人文素養和人文研究,1958年學校在北京成立的時候對這個就有關注,有要求。包括錢學森先生,而且大家知道郭沫若先生是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并不是因為它是一個理科學校,人文生活就非常的寡淡,并不是這樣的刻板印象。
徽派:那么這個手工紙研究所成立的因緣是什么樣的呢?
湯書昆:研究所成立的背景,大致是2004年左右,當時的總書記提出來要關注人文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現代化。這個時候,教育部就啟動在全國高校建類似文科科學研究平臺的國家基地,要有實驗,當時第一批是50個,大概有15個是給理工科學校的,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這個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我當時雖然在學校人文社會學院當執行院長,但是并沒有太過關心這個事情,因為當時的支持是千萬級的,我覺得我們是靠不上的。但是學校的科研處長有一天來找我,說這個基地你們可去申請,支持強度和要求是史無前例的。于是我們去北京,教育部主管的司長一看,你們來干什么。因為按照申報要求你們必須有國家重點學科,而且在全國必須排到前二,最好排第一,第三你就別來了,在他的印象里,你們學校理科是好,但文科是不強的。其實我們有重點學科,就是科學技術史,當時排全國第一,司長很意外,后來我們就合格了,也是因緣契合。
 手工紙實驗室一角
手工紙實驗室一角
徽派:資金支持是底氣。
湯書昆:學院的錢申請下來之后,做什么呢,大家都想參與,但都不在行,所以報了很多計算機,pc機。當時主管校長就調侃我們,你們都國家基地了,還號稱國家第一的,你們就買一堆PC機?其實文科如果按照現在的新文科要求來建,它牽扯到你的思維轉型,平臺與架構的重新思考和設計。當時的校長朱清時院士也兼任學院內科技史和科技考古系的系主任,于是在我們的請求下,他就出任我們這個國家基地的主任。他有科學大項目的經驗,就說我們要凝聚,不是有個想法就海闊天空跑了,當時規劃了好幾個方向,其中在傳統技藝方向提了兩個點——做中國文化中的紙,還有一個是做中國文化中的墨。經過討論,紙和墨形成了兩個研究組,墨因為核心成員離開沒有能研究下去,很可惜,就剩了紙。
開始想研究中國歷代的古紙,后來發現基本不可行,因為古紙樣品都很貴,規范取樣也很難,清代乾隆的紙現在都已經貴到吃不消,何況唐宋的紙,基地的錢加進去也買不了多少張古紙。后來我們討論先成立實驗室,先買些設備,聚合幾個人成為團隊,建實驗室和研究所,系統研究當代現存的造紙工藝,這是最直接的背景故事。
緣起:我們的造紙故事過去沒有講好
 近一千萬字的《手工紙文庫》
近一千萬字的《手工紙文庫》
徽派:線索聽著很清晰。從《手工紙文庫》的調查和編輯開始,您和團隊成員十幾年時間從實驗室走到田間地頭,這個過程,這個研究方向的選擇,和您個人有什么因緣?
湯書昆:實驗室和研究所是公家的,所以是公家的因緣。我自己呢,我們是一個團隊,動態累積到現在超過百人了,我一直作為牽頭人。為什么會做這個事呢,也是因為一種偶然出現的因緣。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期我去日本比較多,每次去只要有時間,我都到東京神田的書店街,有非常多的新書舊書,我主要看舊書,開始不是關注紙,就是舊書打折覺得很劃算,最早買的一套是日本茶道的全集,便宜到完全不敢想。另外,我去過多次安徽涇縣,當時對其它紙沒有概念,但是對涇縣的宣紙有概念。在書店街,我發現日本有很多傳統造紙方面的書,發現日本整理和紙怎么整理的這么好,這么全面。主要是昭和年間,日本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理出版了很多這樣的書。我突然就受到刺激以及啟發。我們也只是知道造紙術是中國發明的,蔡倫是集大成者,但中國從來沒看到這樣的書,確實是沒有,有一些研究文物和考古的。作為造紙的發明國,造紙的起源地,我們居然整理得這么差,這個留了個起心和動念。
徽派:確實是沒有講好這些祖先傳下來好東西的故事。
湯書昆:后來又有一次,參加一個國際交流,描繪全世界的造紙的地方,發現這個地圖上,中國只有一個點,安徽涇縣。日本有10多個點,韓國也有8-9個點,東南亞多國都有造紙點,我就不明白怎么會這樣標呢,中國造紙的地方絕不止這樣啊。所以我們講故事沒講好啊,傳播沒有搞好啊,國際社會的印象就會有問題。那時候就有想法的萌芽,什么時候應該來做一個關于中國手工造紙的相對全的文獻。當時想法很簡單,但沒想到的是經過十幾年的田野調查,發現中國手工造紙到今天依然這么豐富,遠遠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你能夠把本身很好的東西系統挖掘出來展示給別人,是很有基礎意義的事情,這就是另一個緣起。
 實驗室手工紙樣本
實驗室手工紙樣本
徽派:不僅是國外的誤區,其實我們自己也有這樣的誤區,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東西都在這,沒用心珍惜。那真正開始做這個項目是從07年開始的?
湯書昆:對。2008年1月初就出去到云南做田野了。
經歷:田野調查接上“地氣”很重要
徽派:這形成一千萬字文庫的田野調查過程,觸動你的故事肯定也有很多吧?
湯書昆:其實還是你剛才講的那個問題,最初我們自己對中國的手工造紙都不熟悉,因此投入研究工作起始,始料未及的經歷、挫折和發現很多。大家現在看到第一期是十卷一千萬字,還有很多紙樣的采集和分析。實際上,開始我們準備十卷就全部做完,覆蓋全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做研究,田野的一線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能反映真實狀況。目前傳統非遺文化研究體系里,很多類型的系統研究都非常欠缺,屬于快餐式狀態的較多。當時我們想云南、貴州、廣西,三個放一卷應該足夠,因為覺得好像不是造紙重要的地方,應該不會有太多造紙點。2008年1月開始去云南,結果發現云南一個省就夠一本了,貴州一卷根本放不下,要兩卷,這么下來,原先所規劃的十卷肯定做不完,于是才有了二期、三期的重新規劃。這反映了什么呢?中國文化里傳承下來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有相當部分直到目前也還是并不為人所知的。
 《手工紙文庫》內頁
《手工紙文庫》內頁
徽派:中科大在合肥,為什么不從安徽涇縣開始做田野調查呢?
湯書昆:為什么不選安徽涇縣,因為我們想還是先往外面去找,家門口比較容易到達,好像隨時可以去的。那為什么第一站選云南呢?大約2007年夏天吧,我們團隊一個同事看到了一本云南少數民族造紙地圖的小冊子,也是一個旅游的小書,內容比較簡單,但是云南少數民族造紙點已經標注出來不少了。我們發現作者老楊(楊建昆)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是中科院在云南的大同事,能夠先請他作引路人。我們就拉上他,老楊說先去最遠的香格里拉,當時去香格里拉交通非常不方便,顯得比現在遠多了,第一站去了深山里香格里拉縣的白地村。村里的國家級納西族東巴紙傳承人叫和志本,是個老東巴,也就是他們民族的大祭司。老東巴很重視,還特別從縣城請了政協副主席、原先也是村里的干部一起接待。那地方特別漂亮,而且我們過去從來沒看到過這樣的造紙工藝,他是澆紙法,我們也很沉醉其中,但調研時間完全不夠。那一年就是南方大面積嚴重凍雨的年份,到當天傍晚時,政協副主席就對依然在興奮詢問和拍照的田野小組說:你們要走了,縣城前往白地村的路上已經下大雪了,你們只能從虎跳峽這條小路走了,再不走就只能在這里過年了。一再催促提醒下,沒有概念的我們當時七個人,才戀戀不舍地摸黑開夜車離開村子,凌晨12點多到虎跳峽鎮,敲開一家小飯館,請老板重新點火才吃上飯。夜里大雪就過來了,后來據說一個多月才通車,真的是晚一點就要在村里過年了。
徽派:田野調查總是充滿驚喜和意外,需要腳步去丈量和踩實。
湯書昆:貴州廣西的調研都有車掉到深溝里面。其實少數民族村里很熱情,處得來的話,一定要請你吃飯喝酒。所以正常我們都有分工的,誰記錄誰開車誰喝酒,造紙的人都很熱情,少數民族更熱情。很多村長或者叫寨主就說,不喝酒調什么研。
 湯教授團隊田野調研(受訪者提供)
湯教授團隊田野調研(受訪者提供)
徽派:團隊的人都是科大畢業生嗎?
湯書昆:不是這樣的,我們到每個省,都會邀請與組合當地的研究者,這樣會讓我們入手更快、更接近實際。因為初來乍到,熟悉情況都要一陣子,很容易把不住脈的。田野調查必須接地氣,最關鍵就是找到當地合適的人,他們有熱情有興趣有積累,才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采集到有品質的信息。我們在云南不是先找了老楊嗎,后來通過老楊還找了一個白族的年輕人高錦榮,他自己家族在大理的白族村寨里世代都是造紙的,他本人還搞了一個中心在昆明賣紙,我們拉著老楊以及這個小伙子和我們一起走村串寨。如果只帶一幫研究生和老師去,恐怕一段時間都找不著北,他們在家做實驗似乎駕輕就熟,但是田野現場抓住人文信息,抓住工藝信息,這個短時間里是很難的。
特色:研究所和實驗室的工作格式與目標
徽派:那么咱們研究所帶團隊做手工紙項目,和非遺保護相比,我們的特色和目標是什么?
湯書昆:田野工作中,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王海霞老師做了中國年畫大全,做了很多年,我很欣賞她的工作,她對我們的工作也很欣賞。中央美院做全國民間剪紙研究,現在形成了剪紙大全集成,已經是喬曉光教授他們幾代人在做了。當他們和我們開始做類似田野集成型工作的時候,這樣的團隊不多。現在看到成果了,很多人覺得很有意思,但這是需要時間積累的。
 湯教授詳析《文庫》的基本信息構架
湯教授詳析《文庫》的基本信息構架
徽派:所以我們的項目里,人文傳統的部分是如何呈現的呢?
湯書昆:就《文庫》而言,一開始我們是有系統的構思的,從田野調查開始我們就基本想好了要采集什么樣的信息,到現在基本格式也沒有變。我們的格式是:
第一部分,簡明的信息加上兩個地圖——一個到縣域的手工造紙點的歷史與當前分布地圖,另一個是如何到達(你怎么去)的地圖,因為深山里面有可能完全不知往哪去。
第二部分,是強調原生人文內涵的部分,并不強調現代生活如科技對原生文化的介入和改造,我們的科學分析只是提供進一步解讀的新維度支撐,在某些方面達到見微知著,實際上主要是這樣的功能,所以我們第二部分是人文環境和地理環境,會有照片和各種環境特質以及物產、人物等。
第三部分,第三個部分是歷史與傳承,本地造紙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從哪里傳來的?不過這些大部分造紙的人是說不清楚的,可能要找族譜、家譜或者其他秘藏資料。但人家要想,這個給你看是不是合適,這個時候融洽就非常重要,你要進入這個對象的人文情態,象喝酒吃飯就是很重要的溝通方式,喝的高興了你告訴他你要什么,哪些東西是你特別想了解的,他通常會很高興地去想辦法。
徽派:這個也是田野工作的一個重要場景。
湯書昆:造紙人不一定有文化,你要到村里找長老,你要坐得下來才能請長老,一邊喝茶或者喝酒一邊探問,非遺的家族傳承如何如何,這個等于問人家隱私了。
 《手工紙文庫》內頁
《手工紙文庫》內頁
第四部分就涉及到原料,植物纖維的各類原料,造紙過程中的添加如紙藥,各種各樣的植物,需要拍照片,邊疆民族跟我們植物差別非常大。然后測水的酸堿度,造出好紙需要什么酸堿度。《文庫》大頭是工藝流程的記錄,我們想我們的工作還是文獻性為主,我們盡量用的是口述的記錄,盡量少介入我們的態度及觀點,工藝部分我們不加我們的意見,當然我們會印證,會采訪幾個對象來比較,他們所說的工藝和過程是不是有不一致的地方。設施、工具的造型,通常都會有照片或繪圖。這個部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會對這些紙做技術測試,象你們看到眼前實驗室的這些設備用來測試不同的指標,我們設定的書畫類紙的指標和非書畫類紙的指標是不太一樣的。另外對紙的纖維放大呈現,是什么形態特征的纖維,是不是好的纖維,工藝加工是不是有問題,一看就能看到,紙的壽命等等就能看出來,雜細胞還在不在,就是說能不能把純凈的纖維打散分離出來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實驗室大規模測試之前,中國只有極少數的手工紙做過工藝指標的測試,所以我們這個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價值是,第一次對中國手工紙做了系統的科學分析,對于行業、對造紙的人和消費者都有幫助,能夠有助于知其所以然。
徽派:等于把配方弄出來了。
湯書昆:不完全是配方,更重要的是工藝。通過測試分析對工藝加工和原料本身,做一個評判,是有依據的。我們的紙都是在造紙人的家里或廠里買的,采樣可靠,有工藝記錄和原料記錄作印證。田野采樣原始樣本的可靠這個是非常關鍵的,體現了最基礎的科學態度吧。
 手工紙《文庫》內頁
手工紙《文庫》內頁
第五部分,我們做市場、消費、渠道與經濟,歷史上市場怎么樣,過去怎么賣紙,渠道是什么,盈利怎么樣,這種收入在當地是不是覺得還行,也就是說,收入非常低的話就不是好的營生。現在還在造紙的有不少人年紀比較大了,他們也不想改變現在的生活,因此有一定收入還是安心的。
第六部分是民俗傳說故事神話,這是純人文的,讓純人文的造紙人生活中有趣的東西留下來,比如說祭祀,祭蔡倫啊還是誰,怎么祭的,在哪里祭,造紙的人多了會組織起來搞什么活動。
最后一個第七部分就是傳承保護現狀和發展思考,我們把我們主觀的部分放在最后,前面我們不介入只記錄,后面我們會附有紙樣。
原則:不要破壞原生審美的多樣性
徽派:原來我困惑的部分,是新技術和傳統工藝的融合會不會有沖突,現在理解了,其實我們只是在用科學家的技術和態度更好的尊重和保留傳統手工藝最原始的部分。
湯書昆:我們一直強調要尊重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傳承人,這些造紙的人和我們的關系非常好,我們在文旅部主辦的造紙人研修班里建有十個班級群,會經常在群里聊。最近,群里湖南有個傳承人生病,有人幫助發起水滴籌,籌了不少錢。也就是說,我們要保持對經典文化傳統、文化事物和人的尊重敬重,我們在《文庫》里,要一直保持這個態度。避免不良溝通,不會讓他們對做這個事情的人產生很不好的看法,不能說你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出發了,就顯得你認為那個農業社會原生的鄉土文化土氣、不高大上,這是很要命的一個態度。
 手工紙樣本
手工紙樣本
徽派:看到您桌上有很多美學書籍。那回過頭我們看,放下科學家的嚴謹細致,從美學角度,您做的這些工作,最想傳播給大家的是什么?
湯書昆:那不是我的書,是我指導的一個博士的書,他要做這方面的博士論文,從美學角度看紙墨筆硯等傳統技藝。從審美的角度說,你看我們這里有一些紙,云南的、貴州的、西藏的,不少有染色,多數是植物染色。
這個是西藏的藏紙,我們印象里覺得藏紙是粗糙的,但這個藏紙的柔性非常好,伸縮自由度非常好,也不掉色,藏紙做到這個程度,我們很多內地造紙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它有一整套工藝,染色配方也與內地有很大差異。
再看這個紙,也有故事,云南高黎貢山里面一個小村,白族80多歲老太太造紙造了一輩子,為了去那里,我們過金沙江把一個越野車都碰壞了。
這不是刺繡嗎,這是紙上的刺繡,在苗族等等我也看到紙的刺繡做的衣服,還有紙做的帶刺繡的鞋子;后來去貴州從江的侗族,老太太的丈夫曾作為代表到北京給中央領導匯演,老太太60年代用紙做的繡花鞋,還很結實,現在還能穿。過去紙的刺繡是非常流行的,紙做鞋子還能穿你就知道紙的拉力非常好。
從審美的角度說,從調研的基礎上給了我們這樣的提示,盡量保持它的多樣性,在這個基礎上,原地提升,不要把主流的主調的審美范式強度介入到在地化的文化傳承上。你可以提出可改進的地方,手工造紙造了多少代了,原初的基礎在那,讓各路力量有機會介入,就地優化和提升才是關鍵。審美本身就是多樣性,其實也是它的生命。你把本地生發出來的非常豐富多樣的審美用規范統一的面貌破壞掉,這不是我們應該提倡的路徑。新安晚報 安徽網 大皖客戶端記者 蔣楠楠/文 薛重廉/圖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