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皖新聞訊 《東圩埂》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資深媒體人何顯玉又一部紀實散文力作。
荷爾德林曾經(jīng)這樣說:“人充滿勞績,但還詩意的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同樣努力稀釋困厄凄苦的何顯玉,滿懷著“饑餓記憶”的同時也想提供更多向上向善的價值,所以關(guān)于《東圩埂》的人們,他想到的那個詞是:不屈。
5月12日下午,《東圩埂》讀者見面會在安徽省圖書城舉行,何顯玉與著名作家苗秀俠就該作品和文學寫作相關(guān)話題對談。

著名作家苗秀俠和何顯玉對談。
“每一位寫作者都有文學的原鄉(xiāng),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的秦嶺,蘇童老師的香椿樹街,馬爾克斯的馬孔多,何顯玉的東圩埂。”苗秀俠覺得,何顯玉從新聞向文學轉(zhuǎn)身,從城市向鄉(xiāng)村回溯,為文學做足了準備,人生的閱歷,采菊東籬下的耕讀狀態(tài),讀書寫作的氛圍到了,“像古人說的,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
“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推開那扇門,一切好像都沒變,推開那扇門,母親已經(jīng)在另一個世界。我的母親,是老屋子里最后活著的人,她離開之后,我成了母親在這個世界上的遺物。”四年前的谷雨時節(jié),何顯玉母親去世,讓他開始重新感受半生歲月煙火,翻檢往事斑斕滄桑,開荒種菜,晴耕雨讀。兒時伙伴也已倏忽蒼老,隱入塵煙的生活沉到了塵埃里。
這是兒時伙伴的唏噓感慨,也是經(jīng)歷人生迎送俯仰間,何顯玉自己的覺察與體悟,“往后余生,對于生我養(yǎng)我的故鄉(xiāng),是越來越遠了。我已經(jīng)不想要名和利,但我要給東圩埂人樹碑立傳。故鄉(xiāng)和村莊在消亡,我們都會認不得回家的路。但再忙碌,記得回家的路,記得你出發(fā)的地方,記得滋養(yǎng)和鼓勵你,讓你走向遠方的人和事。”
和紅到不行的楊本芬的書一樣,其實何顯玉的寫作,也就八個字:那年那月,那人那事。寫的是屬于何顯玉自己的浮木秋園,豆芝芬芳。“讀紙質(zhì)書的人,對紙墨的香味是有執(zhí)念的。從東圩埂走出來,我像一片樹葉飄零而過,在都市晃蕩一下,現(xiàn)在去山里繼續(xù)和土地親近。唯一不能忘記的,是那個滋養(yǎng)我到十七八歲的故鄉(xiāng)。”在何顯玉看來,靈魂深處,沉寂到最喧囂的,是兒時的記憶,模糊到最清晰的,還是回家的路。
和苗秀俠的相遇,源于2014年《農(nóng)民工》那本書的研討會,苗秀俠和何顯玉有了一個共識,要給如今的人們一個什么樣的東圩埂。文字里不能只有歲月的風霜,更多要給人向上的力量,奮進的自信。“兩鬢染霜的時候,也要知道還有很多路要走。故鄉(xiāng),寫起來可能辛酸。我們的記憶是饑餓,凄苦饑餓困厄太多,淚水血水太多,應該向善向美好出發(fā)。”何顯玉表示,自己家三個姐姐都是文盲,到了自己,才有第一個大學生,“每一個人都有頑強不屈的靈魂,為下一代爭取更多的可能。寫這本書,要寫的是——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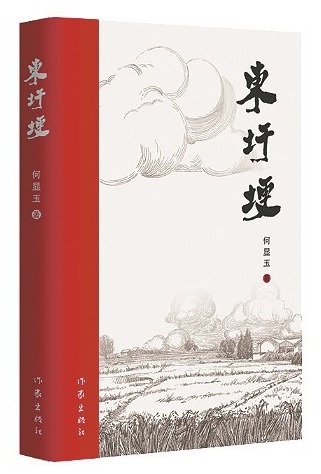
美學大家郭因老,這樣感嘆何顯玉的新書:“《東圩埂》是描寫中國農(nóng)村的一座文化紀念碑。我們從東圩埂生生不息的煙火里,可以看到頑強,看到力量,看到光亮,看到善與美。”
郭因先生的鼓勵讓何顯玉備受鼓舞,也深受感動,“看這本書,可能會猝不及防流淚,但是汲取力量是最重要的初衷。面對郭因老師,你有什么好懈怠的,有什么不應發(fā)奮的,為什么不能因為你的努力,讓世道更美麗。”
郭因老師,是何顯玉另一種精神上的“父親角色”。但何顯玉更難忘記對自己說“在泥巴里摳碗飯吃太難了”的父親,更難忘記那個聽不懂“你孩子的孩子的成績是下中等”的父親,是那個讓自己銘記半生要在學校門口為他喊出“下中等的學生回來了”的父親,何顯玉感慨出了一句金句:“父母沒有太多時光等你人模狗樣。”

從泥巴田里,從高粱地里,何顯玉相信,讀書改變命運。“但是走出來不要丟了讀書兩個字,像以前看《霍元甲》那樣,像以前爭搶著看一本雜志那樣。”何顯玉說,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應該保持那種純粹的熱愛和熱忱。“現(xiàn)在太多東西讓我們眼花繚亂,閱讀變成很碎片化的東西,書籍成了裝樣子的東西,甚至靠讀書走出來的人,裝修奢華的家里,反而沒有書。”
《東圩埂》新書出版時正值臘月小年,像雪夜訪戴,興盡而返一樣,何顯玉踏雪送書也沖上“合肥熱搜”,被戲稱為“寒冬里省城街頭最有溫度的文化事件”。送書,分享,研討,和不同的人交流,何顯玉樂此不疲。在何顯玉看來,文學是照亮世界和心靈的一束光。即便已經(jīng)鬢染風霜的他,愿意竭盡全力地站在那里,成為一個光源。“曾經(jīng)很多束光,照亮我的路。我也愿意成為一束光,去照亮別人的路。”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 攝影報道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