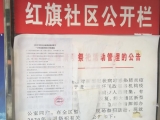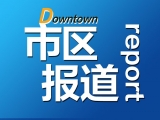凡本報記者署名文字、圖片,版權均屬新安晚報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表;已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使用時必須注明 “來源:新安晚報或安徽網”,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葉大姐,名叫葉玉珍。2019年8月9日,她突發腦梗遠離了我們。
我與葉大姐從認識到熟悉,從相處到往來已經20多個春秋。在這之前,也聽說過葉大姐的故事:那時,她在合肥市二輕局下屬的大集體單位一小商店上班,中午回不去,在省委做領導工作的她愛人,就騎著自行車來送飯,當時晚報有報道,一時間被合肥市民傳為佳話。這件事我印象很深,直到1997年我寫的一篇散文《五一情結》中還提到自行車送飯的事。葉大姐的一生經歷,既簡單又平凡。她1932年出生于廬江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備受苦難。1949年后,她在銅陵礦山當工人時,與女同胞一道繡紅旗、做軍鞋支持抗美援朝。1962年她被下放,1967年成了一名大集體工人。盡管她以后換了不止一個工作單位,但由于葉大姐和她愛人自律甚嚴,以致她的大集體身份始終沒有變,直到退休。
1992年葉大姐退休了,由于她是大集體單位,退休時還沒進行工改,算下來退休工資僅300多元。葉大姐從無怨言,戲稱她的退休工資是三萬多分。葉大姐天生就是個樂天派,她樂呵呵地對我說,雖然只有三萬多分,但我活得很快樂,有錢人家吃大魚大肉,我家就常吃青菜、蘿卜,一年四季,我自己腌制的咸菜餐桌上是少不了的。你看我常年不生病,連感冒都很少有。葉大姐說話時聲音亮,語速快,一句連一句,一口氣說完后便發出爽朗的笑聲。
葉大姐家從來沒有請過保姆,幾十年來,她甘當一位默默無聞的家庭主婦,兒孫都在外地,所有的家務活基本上都是她一人承擔,買菜、做飯、洗衣、打掃衛生等,整天系著圍裙,套著護袖,總是不停地忙碌著。有一次,我看她坐在家門口用搓衣板在搓洗衣服,而洗衣機就停放在走廊上。我走上去好奇地問:“葉大姐,您為什么不用洗衣機?”她隨口應道:“就我和老頭子兩個人的衣服,用洗衣機太浪費水了。”一句話,令我無語,使我動容。一個80歲老人,為了節約用水就用雙手代替洗衣機,若不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說出來真的叫人難以置信。
記得是2012年春天,我在與葉大姐的一次交談中,無意間說出我有孫子了。正在說話的她戛然而止,一把拉住我的手,凝視著我激動地說:“好呀!當年可憐的孤兒(我幼年不幸淪為孤兒,是鄉親們和政府撫育長大),如今當上爺爺啦,兒孫滿堂啦!”最后,葉大姐對我說:“抽個時間,我與老頭子一道去你家看看孫子。”
同年5月22日上午,葉大姐和她的老伴一道,從市里小東門專程來到政務區我的住處,我更是喜出望外。這老兩口已是耄耋老人了,我怎么消受得起?但老兩口像家里的親人一樣,關切地問這問那,問問孩子們的工作,又問問孫子上的幼兒園,又看看每個房間的陳設,葉大姐不由得發出感慨:“你現在住上這么大的房子,有福啊!”我想留二老在家里吃頓便飯,最終被婉言謝絕了。臨走時,葉大姐掏出一個紅包說:“這是給孫子的見面禮(江淮民俗,長輩第一次見到晚輩要給禮物)!”我和家人都表示不能收。葉大姐說,“就兩張,嫌少了就不要。”我一下子被葉大姐的古道熱腸所感動,恭敬不如從命,我和孫子恭恭敬敬地收下紅包。隨后,我在紅包上寫下一行字:“這是2012年葉奶奶給的紅包。”庚子年春節期間,孫子習慣性地整理他的存錢罐,發現了葉奶奶的紅包。我對孫子說,“葉奶奶已經不在了。”孫子好像聽懂了什么,“哇”的一聲哭了。
回憶起來,我與葉大姐相識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那時,她家還住在一幢舊房子里。由于是一樓,光照時間短,家里常年潮濕,直到1998年底才搬到新居。可家具還是原來的:一把小竹椅坐壞了,用塑料繩左一圈右一圈扎牢,至今還在用;三人沙發的坐墊和靠背,有多處磨損,露出里層的包布,大小窟窿無數,坐上去就會粘連衣服。這也引發了前來串門的人戲言:“葉大姐家的沙發,會拉人留客。”幾十年來,葉大姐從基層到省城,環境變了,但她甘于清貧的生活作風沒有變;自己省吃儉用,對人熱情大方的為人處世態度沒有變。這些年來每逢春節,我都要到葉大姐家拜年,我也沒有什么禮物可帶,每次就用塑料袋帶點自家炸的糯米圓子,但葉大姐很喜歡。每次她都會將一大包水果、糕點塞到我的手里,邊塞邊說:“有來有往。”她對人那種真情實意叫你無法拒絕,葉大姐就是處處事事為別人著想的人。
葉大姐的一生,襟懷坦蕩、愛憎分明、勤勞儉樸、與人為善,在她身上體現了一個有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的高風亮節和一個普通女性的崇高美德。葉大姐的一生,又是極不平凡的,我將永遠懷念她、學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