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自己也很喜歡詩集里他認為很有分寸感的《融化到此為止》,他說飽和鹽水里的鹽就在證明“到此為止”。一個朦朧詩的代表詩人,因為病痛,正在面對一個日漸朦朧的世界。世界成了一個漸漸消失的輪廓。梁小斌的一個說法是,是時候打開心靈視角了;梁小斌的另一個說法是,也許自己最好的詩仍然沒有或者終究無法完成。

每一個活著的詩人,時刻都要處在一個警示自己的心弦上
徽派:歡迎梁老師做客我們徽派,梁老師去年新出了一本詩集叫《又見群山如黛》,這個“又見”是什么意思?
梁小斌:從字面上來看,青山如黛是一個偉大的自然現(xiàn)象,簡單講就是江山如畫吧。之所以又見,我個人的體會,古人見到群山如黛和我們當代人見到青山如黛,有一種表面上的不一致。古人見到群山如黛,我猜測,首先都是開動自己的雙腿,展開自己的艱辛,飽覽了群山如黛;當代人見到群山如黛,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我們眾多的國人見到群山如黛,是以旅游的方式展開的。什么叫做旅游的方式呢?就是我們當代人,在我和群山如黛之間,有一個綠色的柵欄。一個綠色的柵欄,在悄悄地呵護著我們游人。在我和青山如黛之間,有一個呵護我們的柵欄,這樣的心態(tài),有時候讓我們的游人就陷入到一種從自我出發(fā)的一個小圈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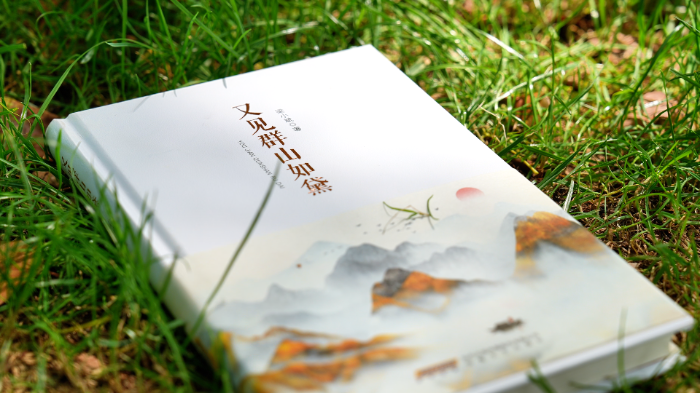
徽派:您剛才說到柵欄,其實您現(xiàn)在和世界之間也有一道柵欄。您剛才說,現(xiàn)在看我只能看到一個大致的輪廓。我不知道眼睛的問題,對您的影響有多大?
梁小斌:我現(xiàn)在的視力狀況,小范圍講,就是不容樂觀吧。但是我個人還在想,要樂觀一下——在視力好的時候,為什么沒有想到“又見”,為什么現(xiàn)在視力模糊了,反而在考慮又見。這里面具體有什么樣的深層含義?除了視覺所見,還有一個心靈所見,至今我才逐漸地、慢慢地體會到心靈所見的群山如黛,對一個人來說大概是尤為重要。
徽派:您一直以來身上的一個標簽是朦朧詩的代表詩人,到了這個歲數(shù),因為眼睛的問題,看這個世界真的變得有點朦朧了。
梁小斌:我們看世界是否朦朧,我個人認為,首先并不取決于我們的視力,而是取決于我們的心靈所見。當視力模糊的時候,才能夠把心靈所見提到我個人生活的日程上來。
徽派:我們很多同事在一起學習了《又見群山如黛》,其中有一首我們印象比較深,《融化到此為止》,就隱約感覺蠻有力量的。
梁小斌:融化到此為止,它的一個最為前提的構思就是,融化沒有到此為止。當一個傾斜的世界,在慢慢變得混沌的時候,我們經(jīng)常講到那種水天一色的境地,就是感到詩人的心緒,將融化在這個水天一色的境地里,而且完全融化干凈,也是我們一種心靈的追求。但是心靈的追求,我個人體悟到,要把一個詩人的心緒,清晰地讓他拗現(xiàn)出來,融化到此為止——不是消解自然,而是一個活脫脫的生命的追求。
徽派:這本詩集里面還有一首詩,我印象也挺深的,就是對“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的解讀,您說它其實不是迎接,是在逃避。您的自序里是這樣寫的,“我有意避開門洞里的雨簾而全神貫注地逃避,卻被別人誤讀成了沖刺和迎接”,在我的腦海里,好像您和海燕重疊了。
梁小斌: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肯定是海燕的心聲,也是海燕的追求;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是一個詩人所看到的一個偉大的景象。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恐怕每一個人都在效仿著英雄的行為,但是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情況存在,當我們效仿英雄的海燕的行為,變成一種曠日持久的行動時,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行為就可能產生某些松懈。在我們日常表達中,我們有的時候把我們行為的松懈,當成了我們行動的堅持。每一個活著的詩人,時刻都要處在一個警示自己的心弦上。

我們的心靈,在詩歌的某一個片段里永遠地駐扎下去
徽派:書的自序里邊,您說您其實是一個“大隱于市的學徒”。
梁小斌:大隱隱于市,實際上是一個崇高的詞匯。崇高的詞匯不是固定在書架上,或者固定在野外某一個地方,好像我們把它翻開,我們把它拾起來,我們就掌握了這個真理。實事求是地說,大隱隱于市,我也是在一個不斷的追求、不斷的困惑過程中。一個人,他只要每天早晨從家里面出去,他的形象就在不斷地轉換,他要去超市,他就成了一個顧客,他要去銀行,他就成了一個儲戶。所謂大隱隱于市,就是隱于我這個人的稱呼不斷的改變之中。我個人認為,他總是在不同的環(huán)境里真實地拗現(xiàn)出來,展現(xiàn)了一個人的形象整體。簡單來講,在大隱隱于市的不同的環(huán)境中間,怎樣突出地展現(xiàn)一個人的面貌,是我的追求。
徽派:我們來之前讓DeepSeek以《融化到此為止》為題,寫一首梁小斌風格的詩。您覺得它寫得好不好?
梁小斌:小范圍講,剛才你念的這首詩寫得好。
徽派:哦?您沒有否定AI的創(chuàng)作。我不知道您怎么看AI這個作品給人的這種堆砌感?
梁小斌:語言的堆砌是我們把任何語言任意地組合,有時候一個寫作方式所造成的詞語的任意堆砌,可以產生一個意外效果。嚴格意義上來講,還不屬于我們心靈的勞動成果,我們在語言的意外效果里面。因為這首先不是我們的勞動所得,所以我們在意外效果里面,也不可能長時間的逗留。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想,詩歌分三種意境,第一是逗留,第二是駐扎,第三是永駐。我們的心靈在詩歌的某一個片段里永遠地駐扎下去。

讀詩是對一個人心靈的安慰,讀詩有百利而無一害
徽派:您覺得在這個年代,一個人為什么要讀詩?
梁小斌:讀詩可以肯定地說,是對一個人心靈的安慰。讀詩有百利而無一害。我聽說一個故事,知青把老鄉(xiāng)的雞摸回來,煮熟就吃掉了。我就想把這件事變成是我做的怎么辦。可以想見,雞的香味彌漫在夜半的村莊里,這個“壯美的景色”引起了我深深的寫作欲望,我就把自己演繹成一個偷雞的人。于是我寫了一首詩:雞的芬芳,正大步疾走。這雞的芬芳像什么呢?這個關鍵的形容,就是講到我們的語文造句能力。雞的芬芳,正大步疾走,猶如戴著紅色羽冠的翩翩少年,騎著白馬,在天亮之前,將他被殺害的消息通知千家萬戶。丟失了雞的老鄉(xiāng)肯定要出來尋找,但我們都睡著了,就在這個時候一陣風刮來,我一躍而起,要擋住那個翩翩少年,但是一個嚴峻的事實是,雞的芬芳是擋不住的。當雞的芬芳在整個村莊彌漫的時候,我想到最后一句話,不知道跟這景色是相悖還是相容的一句話——我在心里面說,該放鹽了。
大皖新聞記者 蔣楠楠
編輯 崔恒





請輸入驗證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