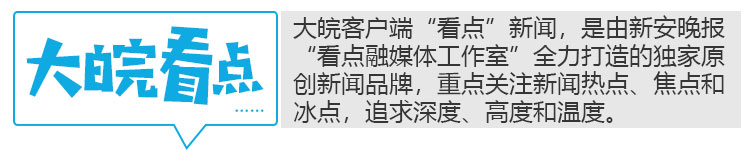
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訊 10 月19 日,“魔芋大王”、安徽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何家慶因病在合肥去世,享年70 歲。很多人都知道何家慶曾自費扶貧大西南,歷時300多天行程3 萬多公里,推廣魔芋栽培技術,但很少有人知道,3 年前為了讓我國栝樓產業發展更好和幫助農民增收,67 歲的何家慶再次自費上路,出走皖、蘇、浙、贛、豫、鄂等多省山區,調研栝樓產業現狀,推廣科學栽培技術,最后暈倒在調研路上。
10 月17 日,在去世前兩天,何家慶在醫院病床上接受了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記者的獨家專訪,講述了近10 年來的經歷。

10月17日,在病床上接受新安晚報記者采訪的何家慶教授雖已極度虛弱,談起自己的“栝樓扶貧”心愿仍是精神一振。

去世前兩天,何家慶在病床上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自費扶貧大西南,被贊“魔芋大王”
1949 年出生的何家慶是安徽安慶人,1972 年到1975 年在安徽大學生物系學習,隨后在安徽大學生物系工作、任教。何家慶一直致力于植物資源的研究和科學利用,從而助力資源植物的產業化發展,幫助農民增收。1984 年,何家慶自費考察大別山植物資源,考察報告為中央實施山區星火計劃提供了依據。1998年,何家慶自費扶貧大西南,歷時300 多天,跨越8 省區,行程3 萬多公里,為100多個縣的芋農講授了魔芋栽培技術,被稱為“魔芋大王”,還獲得了全國勞動模范、全國扶貧狀元等榮譽稱號。2000 年4 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在合肥接見了何家慶。
2010 年1 月,何家慶被安徽大學延聘3 年。2013 年年初,何家慶受聘成為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植物標本室主任。何家慶告訴記者,他在安徽大學工作了40 多年,對安大感情深厚,師生之情也難以割舍,但從植物學研究的角度出發,他還是去了南大。在南京大學植物標本室,他的具體工作主要是標本的鑒定和數據化處理,“數據化處理很繁雜,需要嚴謹。”何家慶說,首先要確定標本的采集時間、地點、采集人及生物特征,然后再進行嚴格鑒定,“比如屬于哪個科,哪個種,哪個變種等。”另外,何家慶還要對標本刷科學條碼,并拍攝不同角度的照片,“然后才能納入數據化處理庫,缺一不可。
不忘初心再上路,力推“栝樓扶貧”
南京大學植物標本室里看似枯燥的工作,何家慶卻做得津津有味。他告訴記者,做這項科學技術鑒定工作是要有責任感的,“不僅是對現存的標本負責,也要對日后的科技工作者負責,所以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和不認真。”在鑒定標本的同時,何家慶還對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學生的野外實習進行了指導,他認真的態度和豐富的知識經驗,贏得了學校和師生的認可,經考核后,南京大學決定對他續聘3年。
雖然和南大相處得非常融洽,但已經65 歲的何家慶心里卻按捺不住另一個沖動,“我做了一輩子的植物學,還有一個心愿未了,那就是栝樓產業。”栝樓是葫蘆科栝樓屬植物,別稱瓜蔞,延續至今有千余年歷史。自古以來,栝樓在我國被用作中藥材,也為食料、護膚品等,用途廣泛。研究證明,栝樓籽含有多種不飽和脂肪酸成分,且比重大,對人體健康具有一定益處。
可以說,栝樓作為一種藥食同源的經濟作物,一方面有著很高的營養應用價值和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其適應能力強,有廣泛種植的推廣潛力,是一種很適合產業化發展的植物。但是,何家慶了解到,目前國內的栝樓產業發展還存在技術、市場調控、資源評價體系等諸多問題。所以,他希望像當年傳播魔芋科學種植技術一樣,再次上路,讓栝樓產業得以更好地發展,為老百姓謀福利。“將植物資源形成產業化,也能推動我國現階段農業的生產水平,形成更好的國際競爭力。”何家慶說。
老教授出師不利碰了“一鼻子灰”
何家慶對于栝樓資源產業化的思考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10 年的積累和準備。何家慶告訴記者,在這10 年里,他做了一些基礎工作,“首先是出版了《中國栝樓》這本書,記錄了全世界80 多種栝樓,包括國內的62 種,匯聚了大量有關栝樓資源的資料。”同時,這10年里,何家慶還搜集了全國各地栝樓栽培區、栝樓園的分布情況及栽培管理現狀等。另外,他還獲得了國家知識產權局有關栝樓的6 項發明專利。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感到有一種社會責任的壓力,我要把積累的這些知識和經驗,傳遞給與栝樓資源產業化相關的社會生產者。”于是,2016 年,67 歲的何家慶向南京大學遞交了假條,懷揣著對栝樓產業的10 年積累和一顆為農民扶貧增收的初心,踏上了自費“栝樓扶貧”之路。第一站,何家慶選擇了江蘇宜興。“出發之前,我在網上搜索了很多,看看哪些區域栽培大戶和農場主、企業更多,哪些區域的種植傳統更加悠久,還畫了幅圖。”何家慶說,他是個老師,不是生意人,做這件事是自費,不帶個人利益訴求、不收一毛錢,應該會得到栝樓相關企業、栽培大戶的歡迎,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理解和支持。
但現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順利,何家慶先后在江蘇、浙江等地碰了壁。“有的地方是結構調整不再種植栝樓,有的地方對我說的不感興趣。”何家慶說,一路上他還是跟以前一樣,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和草鞋,胡子拉碴、頭發很長,住在最便宜的招待所,“有一次我在長興找到一個企業主,他盯著我看了很久說‘你不是教授嗎?怎么這個樣子,連車都沒有。”

偶遇知己精神爽教授“傾囊相授”
就這樣,何家慶一路從江蘇走到安徽,又從安徽走到浙江,隨后又來到江西省九江市武寧縣。“一開始他們不認我,后來一位名叫汪光明的高級農業師來了,跟我聊起了栝樓,才認了我。”何家慶說。何家慶總算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聽汪光明介紹了當地栝樓種植情況后,他渾身充滿了動力,“汪光明告訴我,之前雖然種植了栝樓,但對于國家政策、未來方向都不太清楚。和我聊過以后,他對栝樓產業的未來發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何家慶告訴自己,就算遇到再多挫折也要把栝樓調研做下去,這樣“才能對得起這些在基層努力工作的栝樓人”。隨后幾天里,何家慶坐在汪光明的電動車后座上,跑遍了武寧縣的栝樓園。而一路上顛簸,也讓這位67 歲的老人苦不堪言。晚上住宿的時候,汪光明將何家慶帶到一間旅館。問過價格后,對栝樓產業侃侃而談的何家慶,卻突然有點羞澀地問能不能找間更便宜的。汪光明很奇怪地問他:“168元,還付不起嗎?”何家慶只好低聲說:“我是自費的。”于是,倆人找到了一間條件更差但只要80 元一晚的旅館,何家慶這才安心住下。
在武寧縣的一個多星期,雖然住得簡陋、行得艱苦,但何家慶卻充滿了熱情,他將所學和積累傳播給了當地的種植大戶和農場主,指導他們科學栽培,“栝樓是多年生作物,一年種下去,本來有四五年的收成。但有的人用水太大太猛,栝樓就會澇死,還會出現病蟲害。另外,栝樓喜歡砂性土,但有的人用的是粘性土,也不好。
一年調研十七省遍撒栝樓“種子”
離開九江市武寧縣后,何家慶又獨自前往安徽、河南、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多個地區開展栝樓調研。從他的《一個植物學教學、研究者對中國栝樓產業調研后的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從2016 年4 月18 日至2017 年2 月11 日,他持續工作300天,途中病倒22 天,對我國17 個省(區) 166 個縣市的149 個專業合作社及家庭農場、26 個國家農場與工業園及生態示范區、103 個企業及公司進行了科學調研;行程48900余公里,其中步行5860余公里。
通過這次實地調研何家慶發現,作為中藥材的栝樓栽培區,多在淮河流域以北;而作為食材栽培區,目前連片面積集中于安徽大別山區、江西九江市下轄各縣市、貴陽周邊、蘇北平原、山東沂蒙山區及秦巴山區,“這些地區多為貧困山區。”通過調研,何家慶也發現了栝樓栽培中的一些實際問題。“目前大多采用的還是老技術,導致了產品退化,果子越來越小,果子里的種子越來越少,籽粒越來越不飽滿。所以,有的縣都已經不種了。”何家慶說,另外栝樓苗需要年年更換導致產量降低,以及病蟲害嚴重,也挫傷了栝樓種植戶的積極性,“一些老百姓覺得不好種。”
對此,何家慶沿途不斷與地方政府工作人員、主管部門技術人員、栽培大戶及企業主進行交流座談,還舉辦了幾十場不同形式的座談會、技術培訓會、專題報告會。岳西縣農委多經站站長王德河告訴記者,何家慶自費前來該縣,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去瓜蔞種植基地和加工廠實地考察,也會對從業人員進行義務指導,“他來到大山深處看了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我們陪同了,也有不少地方是他自己去的。”
潛山市栝樓產業協會會長王傳文告訴記者,這幾年何家慶給潛山的栝樓產業發展出了很多主意,還在潛山開了培訓班,不僅在繁殖種苗、病蟲害防治等方面對從業人員進行了系統培訓,還提出了不少栝樓深加工方面的建議,比如開發栝樓飲料、研制醫藥中間體等,為當地從業人員開拓了視野。
扶貧路上未竟事希望學生“接棒”
3 年來的風餐露宿和艱苦奔波,讓何家慶的身體逐漸有點吃不消了。2019 年7 月,在潛山一次栝樓產業調研途中,何家慶突然暈倒在正午的烈日下。送醫后,他被查出癌癥晚期。在資源植物產業化和扶貧道路上奔波了幾十年的何家慶,只能停下腳步,住進了醫院。
安徽農業大學博士后王強曾于2009 年到2012 年跟隨何家慶老師讀碩士研究生。他告訴記者,何老師充滿想象力和活力,對學生非常好,也鼓勵學生動手解決問題,而不是受限于固定模式,“他對弱勢群體有很強的同情心,所以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更多貧困農民謀取福利。”王強說,何老師去世前的幾個月,還在跟以前的學生交流栝樓產業的發展,“希望我們能對栝樓有更多了解,并能總結出一個模式,再去開發更多的資源植物,為百姓謀取更多福利。”
何家慶女兒何禾告訴記者,父親去世前已經無法進食,只能用湯勺喝水,靠打營養針維持生命。因為疾病,何家慶雙腿浮腫,每天都得忍受著巨大的疼痛,“即使這樣,他還躺在病床上盡力寫調研報告,希望把更多的調研所得傳遞給我們。”
本組稿件由 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客戶端記者 項磊 王從啟 余康生 攝影報道
何家慶獻出眼角膜 希望捐給山區貧困娃
記者昨天從安徽省紅十字眼庫了解到,10 月19 日晚何家慶去世后,按照其生前遺愿進行了角膜捐獻。據介紹,何家慶生前向家屬提出,要把眼角膜捐獻給山區貧困孩子。
安徽省紅十字眼庫主任屈志國告訴記者,何家慶生前囑托家屬,一定要把眼角膜捐獻給山區的貧困孩子。“他患的是癌癥,全身器官只有眼角膜可以捐獻。”10月19 日晚,何家慶教授去世后,安徽省紅十字眼庫工作人員辦理了相關角膜捐獻手續。屈志國說:“兩個角膜非常透明,正在遵照何老師的遺愿尋找受者。”
生平簡歷——
何家慶,男,安徽省安慶人,1949 年12 月出生。1968 年11 月至1970 年12 月在望江縣蓮洲公社參加工作,1970 年12 月至1972 年9 月在安慶市醫藥公司工作。1972 年9 月至1975 年7 月在安徽大學生物系學習。1975 年7 月至1990 年6 月在安徽大學生物系工作,1990 年6 月至1993 年9 月在安徽省績溪縣擔任科技副縣長職務,1993 年9 月至2013年6 月在安徽大學生物系任教,2000年12 月獲評教授職稱。2010 年1 月被安徽大學延聘,2013 年退休。
何家慶先后從事植物形態解剖學、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物學、資源植物學、植物生理學及植物化學等課程的教學工作,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其中國家核心期刊15 篇),出版專著多部,譯著1 部,合編2 部,獲科技進步獎2 項,創造發明專利10 余項。1992 年獲安徽省勞動模范稱號,2000 年獲全國勞動模范、全國第七屆扶貧狀元稱號,2001 年獲評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師德先進個人等,2002 年獲評安徽省扶貧二等功等。2019 年10 月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周年”紀念獎章。
記者手記——
10 月中旬,我們聽說,何家慶老師這幾年一直奔波在路上,在一次調研中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在很多人眼中,何家慶稱得上“傳奇人物”,本報也曾多次報道他的事跡,所以我們也很想再次了解這些年來他的經歷。通過他的學生,我們約好了采訪時間,并于10 月17 日在醫院見到了何老師。
當時何老師躺在床上,想稍微起身都無法做到,只能在家人幫助下半靠在疊起來的被子上。這個曾經在無數山區歷經無數艱難困苦的剛強漢子,這一刻卻忍受著巨大的病痛折磨。但是他居然還在堅持看材料、寫調研報告,他想在最后的時間里,多留一些東西給后人。何老師對我們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歷,那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從安大退休后,他前往南京大學,繼續從事喜歡的工作。對一個已經60 多歲的老人來說,這難道不是一個舒適的晚年嗎?但是何老師初心不改,再次上路,選擇了艱苦奔波的扶貧路。他多次碰壁,風餐露宿,到過最遠的山村,住過最便宜的旅館,為的是將自己10 年的積累付諸到實踐、幫助農民增收、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
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是,何老師的思路還很清晰。雖然說一會要休息一下、喝點水,但他一直堅持接受采訪。在對我們說了一個小時的經歷后,我們再也不忍心讓他繼續說下去,只想讓他躺下來休息,心想過兩天他好點了我們再來采訪。
可是,這終究還是成了一次沒有完成的采訪,卻記錄了何老師最后的講述內容——10 月19 日深夜,何老師去世的消息傳來,悲痛之余,我們只能將他講述的這段并不完整的經歷,展現給關心他的人。
我們知道,這3 年里,何老師還有很多的經歷、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收獲和未了的心愿……可我們已經無法再聽他講述了。但是,何老師的一生,已經留給社會足夠多的財富了。我們不會忘記他,而是以他為鏡不斷反思自己,以他的精神作為前行的動力和支撐。
這次采訪,我們終生難忘。
愿何老師安息。
本文由大皖新聞客戶端獨家出品,不在新安晚報版權授權范圍之內。未經特別授權,不得轉載。
轉載拒絕任何形式刪改。
本欄目常年法律顧問:安徽天禾律師事務所 陳軍





請輸入驗證碼